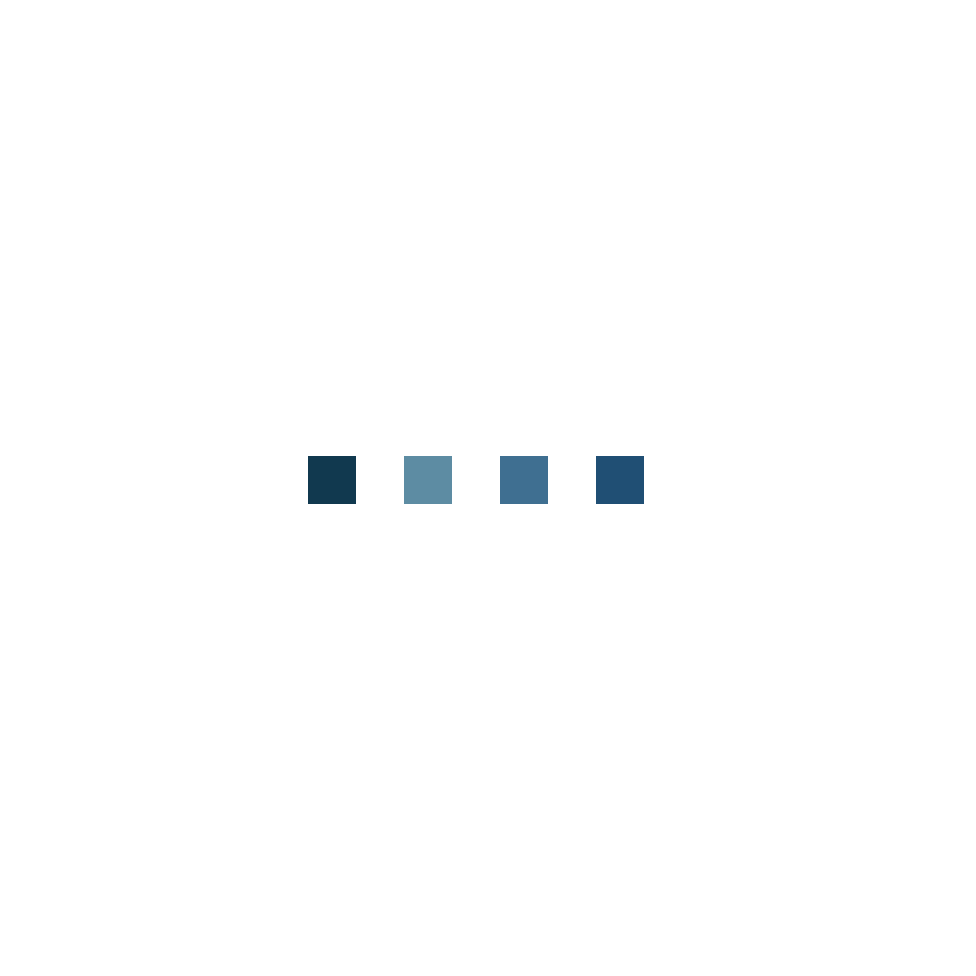行過死蔭之地找答案
其中一個她必須一再回答、廓清——來自他人,也是她自己的——疑問:為什麼要一直寫懸疑/犯罪小說?《摩天大樓》以降,接連出版《無父之城》、《親愛的共犯》、《你不能再死一次》,用一本一本的節奏挨近犯罪小說的框架;一開始是單純懸疑元素,接著出現偵探查案,最新的《你不能再死一次》更有了連環殺人事件。確實讓人好奇,她孜孜矻矻研磨謀殺巧藝是為何?
陳雪的回答是,「為了逼近答案,」她對這答案的回答是「面對罪行我們該怎麼辦?」人性如迷宮複雜,也能同繁星不朽,但人很難專注探索——在這短影音、OTT夾擊,長篇小說讓作者跟讀者都案牘勞形的時代。因此,陳雪說,需要「用犯罪小說的鉤子」讓讀者願意進入迷宮仰望星斗。
進入之後呢?「我想知道殺了人,會變成怎樣的人?或者說殺人的動機,有沒有可能殺人者到最後一刻才知道自己為何這樣做?表面上這惡行很極端,但我們不也常常遊走在惡行的邊緣嗎?去探究理解即將走向極端的人,是不是能拉回一些人?」前陣子事件視界望遠鏡拍到了黑洞,陳雪也在做一樣的事,丟出犯罪小說的鉤子到深不見底的地方,悄聲問,還有人在這裡嗎?
從「純文學」出發寫懸疑犯罪,陳雪是孤獨的。「寫《摩天大樓》時,有個朋友說他不懂我為何會從《迷宮中的戀人》變成《摩天大樓》,他始終沒告訴我他的納悶是什麼。好友看了我後來幾本小說,只說:『你會的是我不會的。』之後也很難再討論。有一段時間,好像朋友們都不知道我在幹嘛,那段時間我也會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好像跟好朋友已經不是同一路的人了,我不知道可以跟誰討論小說創作。這種感覺讓我很困惑。後來我只能告訴自己,我是在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只能靠自己摸索。」說完,陳雪想了一下又說,「可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寫罪行啊。」
犯罪的美麗新世界
不過這句補充透露當我們討論純文學跨足類型,必須很小心,稍不注意就會落入誰主誰次、有尊有卑的二元窘境。陳雪自己也明白,「我很怕自己有寫懸疑小說是在降低自己的感覺,相反的,我是在寫懸疑/犯罪時才發現小說的邊界。」
「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類型或犯罪往往被看輕,那它為何很難寫?我自認是專業小說家,還是覺得很難,甚至不斷問自己為何要寫這個,我到底適不適合寫?這讓我思考,答案或許在小說自身。類不類型、純不純文學是小說方法的不同。」
「所以問題是,到底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去寫(犯罪小說)?」這或許是訪談中這麼多問句裡,陳雪最渴望知道答案的。

為了寫懸疑犯罪,陳雪重新學寫對話。這件事過去讓她焦慮,「我們習慣用風格化的敘述推動劇情,但犯罪小說需要對話。進入對話後,角色說話要有個人特色,日常的感覺,不能風格化。同時,對話不像描述,很難用漂亮的文字,只能用基本功。這提醒我戒除對文字的依賴,讓文字更中性。文字不只是服務作者。」
犯罪小說仰賴的框架或者說套路,一度也是陳雪的心魔。「我知道要有套路,但常常想不落俗套,所以會陷入猶豫矛盾。」從《無父之城》到《你不能再死一次》,犯罪小說的痕跡更明顯,陳雪的說法是「終於擺脫心裡的包袱」。寫犯罪,表面上是跨界,實際上是再發現,發現小說別有洞天,發現自己還能寫,「我才50歲欸,還有扣打,可以去學習新東西。」
回到植有桃花林的小鎮
《你不能再死一次》有個華美的死亡開場,少女陳屍在盛開的桃花林中,「花瓣墜落於發著短草的地上形成一片花毯,花毯中盛開著一張少女的臉。」死亡混著花與青春,禁斷的甜膩氣息。不久,女主角父親被指認是凶手。父親被捕後自縊,她因此家破人亡,遠離家鄉。14年後,同樣的犯罪手法再度出現,女主角被迫回到家鄉,直面桃花林中的黑暗。
相較前2本,《你不能再死一次》有偵探,有辦案過程。更重要的是,有凶手——一個連續殺人犯——的模樣。陳雪不諱言,寫這本是她創作以來最痛苦的一次,「這本小說的最大功臣是阿早,小說來自他想到的書名,我才從這書名去想怎樣的情形不能再死一次。」過程中,伴侶阿早怕陳雪寫不好,不斷跟她討論,「去年5月我把初稿給阿早看,被他退稿。之後我跟阿早睡前都在討論小說要怎麼寫。他以一個愛人的心情擔心我寫差了,兩邊(純文學與犯罪)不討好,連他都說你還要寫這個嗎?但我是一個很固執的人,所以這本改了5個版本。交稿後我心裡只想,我不想再改一次。」
所以,寫犯罪小說,除了擺落文字習慣,學習套路再反套路,陳雪還學到了一件事,「以前我覺得寫小說就是一個人的事,這次的經驗很寶貴,打破了我的想法。」過程中,有件事讓陳雪記憶猶新,「有個段落我一直寫不到位,阿早就放了徐佳瑩的〈人啊〉給我聽——因為我平常寫作只聽古典樂。我是很少哭的人,寫到最後,我哭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演員,在扮演自己寫的角色。這時候我才想到,過去寫純文學我不會脫離自己太遠,但寫犯罪不一樣。」
從創作者變成自己創作的角色,這一回,還包括連續殺人犯。「我想寫非一般的殺人者,琢磨這樣的人的心態。以殺人者當第二主角比較少見,所以我放了很多篇幅在這角色上,因為要夠曲折,夠層層疊疊才能逼出罪行對人的影響,又是什麼導致的。」
陳雪的創作姿態,讓我想到英國作家薇兒麥克德米。同是女同志,同樣書寫謀殺,描摹暴行。薇兒麥克德米過去常被非議,為何要寫得這麼殘忍呢?自稱見血會昏倒,卻努力在小說裡殺人的她回道,女性本來就生活在危機四伏中,時時都有可能遭受侵犯。因此,女性書寫犯罪更能從當事者角度感受,並度人以這感受。
再狂野追尋一回
回到陳雪,她更從加害者的角色出發,帶給讀者原來愛恨互為表裡。這也回到一開始陳雪的疑惑,戀愛教主為什麼一再操演犯罪?「很多讀者習慣看我的臉書寫戀愛故事,可是讀完那300字後,就像喝雞湯也不會長肌肉。不被愛,不愛自己小孩,因為愛做了錯誤決定,或者愛怎樣拯救自己,都是讀小說才能有的體悟。」陳雪是小說之神鍾愛的女兒,因為她仍信仰小說的力量,「小說讓我們擁有無法度過的人生,透過閱讀,你逐漸經歷別人的人生,而被改變。即使你從小到大都待在一個很小的地方,讀了很多小說,你就能穿透世界。」
因此,陳雪左手寫戀愛課散文,右手寫出《無父之城》是小我的愛遇到國家級暴行的下場;《親愛的共犯》是彼此相助如珍珠項鍊般串鏈的珍貴之心;而《你不能再死一次》則是當愛被誤譯的悲劇。
陳雪坦言,一開始不大喜歡戀愛教主跟犯罪女王這類標籤,「但後來我覺得也滿酷的,而且它們是有共通的,都是關於愛的想像。小說裡,我儘量讓讀者可以找到一個站立的地方,不要站在流沙上。回過神,人會發現自己是可以穿越這些殘酷無情的。」
一手寫戀愛,一手寫不被愛,需要精巧而調節的平衡感。陳雪說,現在的穩定生活,給她這樣的寫作力量。「以前的我沒辦法達到這種平衡,因為以前我就是談戀愛與無止盡的幻滅,不斷找下一個人。我會想,難道人只能互相勾引,狂愛後背叛、分離嗎?難道愛情沒有另一種可能嗎?這樣想才意識到,我以前的生活也是一個套路啊,我用現在的生活證明了,人可以反自己的套路。」

訪問前夕,陳雪以《親愛的共犯》獲書展小說獎大獎。我問她有何感受,陳雪回答,得獎讓她覺得好像可以再寫一本;寫犯罪,終於感覺自己不是出界了,而是在拓展身為小說家的邊界。
邊界落在哪?小說家其實走過。陳雪說了一段故事,「前陣子《惡魔的女兒》重出,我才發現裡頭都是對話,阿早就說不是你不會寫對話,只是忘記了。我想對啊,如果世界上沒有我的價值,我應該要自己定義。當初《惡女書》連出版都差點沒辦法,為什麼我到了50歲,寫東西要綁手綁腳?我應該再大膽一次。」
這次訪陳雪,是我聽過受訪者丟出最多疑問的一次,也是透過疑問獲得最多力量的一次。我想起羅貝托博拉紐一首關於偵探的詩,遙遠回應了陳雪不斷探問的小說的邊界:「我夢見迷失的偵探/在阿諾菲尼夫婦家的凸鏡裡: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視角,我們的恐怖模型。」
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視角,我們的所懼怕的,都構成了小說家的邊界。陳雪是博拉紐夢見正尋尋覓覓的偵探。
《你不能再死一次》新書正式上市,購書請點>>>https://reurl.cc/6Zde4V
《你不能再死一次》於鏡文學官網刊登,試閱請點>>>https://bit.ly/3NyS4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