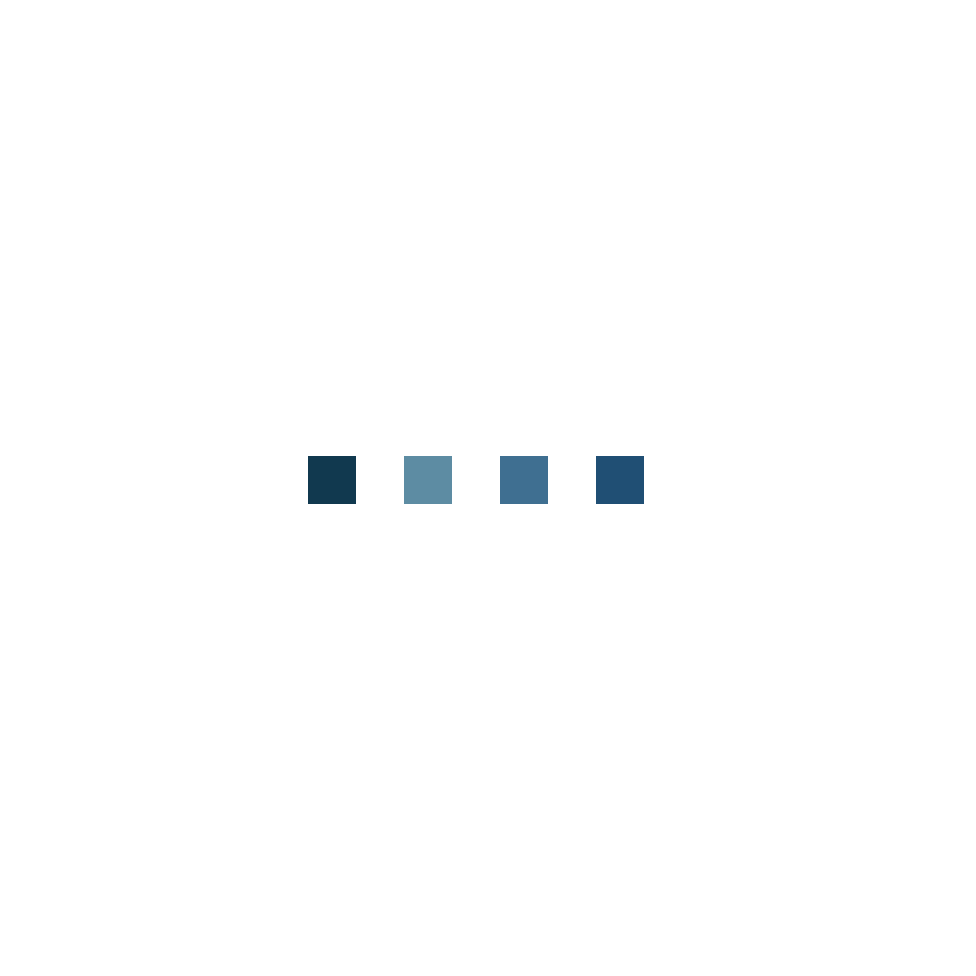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回家一次〉蕭鈞毅全文朗讀
他記得這樣的畫面:一炷香、一盞明滅的紅燭燈、一架神桌、一尊被燻黑肩上黏了致贈金邊巾的媽祖、一籃水果、一袋長金紙對折放在夾層、一名哭泣的老婦、一個站在旁邊面露愁容的臃腫婦人。他記得這樣的畫面,並沒有給他的生活帶來任何寬慰。他惘惘回頭,從褪白與泛黃的牆面上嗅到多年以前一直都有的沉香,是線香的氣味,這一間屋子裡頭早就沒有人了,東西還停在原地,時鐘無聲,水龍頭栓得緊緊的,每一步踏下去都有沙沙的隔閡感,他戴著口罩。
李先生說:「你進去以後,不用擔心家裡。」李先生按著他的肩。他漠然沒有多說,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好久了。他踢開一顆天花板油漆的破片,噢,「李先生,真是謝謝你了。」他想起來,他已經把自己的家交給了李先生。
弟弟的腳踝瘦瘦乾乾的,像雞骨頭,他擔心一壓就碎。
他掛心他後來被正名為學習障礙的弟弟,害羞、內向、不善言語;自己的父親從他們還小就愛找弟弟麻煩,他在父親酒瘋就帶弟弟跑出屋外:要追我就讓你來追。他背著弟弟在竹林裡跑,臉頰都是割傷,父親追不到了就在山林裡大吼,怨你們是野種,怨你們是狗娘養的,怨你們不讓我好好管教,將來要飯行乞。誰會相信──他這麼想,他問弟弟累不累,弟弟搖搖頭,弟弟好輕,每一次他摸到弟弟的腳踝,瘦瘦乾乾的,像雞骨頭,他擔心一壓就碎。這樣跑久了他就習慣把一條毯子綁在腰際,在家裡來來去去的,父親看到他腰際就罵,他也不管,因為跑到竹林還有毯子可以蓋。兄弟倆都不多話,不要凍著就好。他擔心他的弟弟,特別跟李先生說:「文強拜託你多多照顧,可以的話,幫他找份工。」李先生低著頭抽菸,點點頭說好。
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進去了。
「媽媽那邊就麻煩你了。」
「當然,當然……等你出來,我們再看怎麼樣,幫你找個工作。」
「謝謝。」
他走進廳堂,抱著哭泣的外婆,外婆的哭聲他記不起來,在紅色的燭燈中晃盪的是一半泛紅,另一半在黑暗中的外婆的臉,他和外婆簡單交代幾句「要保重身體。」「等我出來再替妳作壽。」像哄小孩,他一瞬間覺得自己像個大人了,和外婆當年哄著自己一樣:「毋人會再打你。」這聽起來真甜,但聽自己的話卻硬巴巴的,和疏鬆的骨頭相互磨蹭一樣,話語中掉下的只有絮粉。
那陣子在工廠他都笑著,同事以為他交女朋友了。
過了幾年,外面寫來外婆過世的消息。他沒有說話一整天,放飯的為他多加了點餐飯,戴帽子關門的偷偷遞給他幾根菸:他就在不透光的房裡抽了起來。
那是悲苦。他會這樣想,又會阻止自己這麼想。回到這個家,除了沒搬走的,搬走的都是他的觸感、嗅覺、與柔軟的部分。留給他只是以無法動搖的黏著姿態,牢牢地攀在牆面與地基,這些無法搬走的部分,就如同他還能夠「記得」,這是無法剝奪的事。
他壓著自己的帽沿。
文強的房間裡還有留下來的床被。被蟲蛀了,日記本也被蟲蛀了,好多個歪扭的字都被吞掉大半。文強很大了才終於能好好寫字,很醜,可是能說,幾個字就是一天。他從頭教起:「先寫日期。」文強就寫日期,「再寫天氣。」文強走到屋外,再回來:「大太陽。」「寫晴天。」「晴天。」文強寫成了「情」,他替文強改:「是這個晴,一個日,一個青。」一筆一畫握著文強的手。「再寫你今天發生的事。」文強寫下「今天發生的事」,他就笑了:「我是說你今天遇到什麼人,有什麼事情可以紀念,不是叫你寫這幾個字。」文強抬頭困惑地看他。
後來文強可以寫下:「一月十日,陰天,今天我吃了魚湯,好吃。」這樣的句子,他很高興,那陣子在工廠他都笑著,同事以為他交女朋友了,一直盧他介紹一下,大家出來吃個飯,一起去夜市玩;他說不是,還沒有人信。
他每天晚上都會回家看看文強的日記,寫得好的他就帶零食給文強。
「二月九日,晴天,哥哥給我新衣服。」
「二月十二日,晴天,哥哥帶我去夜市。」
「二月十七日,雨天,哥哥帶我跟婆婆去工廠。」

火星翻飛,他一直隱忍的恐懼在彼時才雨點般湧上來。
他伸手抹去日記本上頭的灰。屋外有光進來,院子裡爬滿了藤,再殘破的光也能讓它們生長。
他剛進去的時候,見到大門有人燒著金紙。一爐火在夜裡盤桓,有風從裡頭挖去了火屑。火星翻飛,他一直隱忍的恐懼在彼時才雨點般湧上來。身體忍不住顫抖,他們對他說:「嘿,殺了人現在才會怕。」
是啊。現在才會怕,因為我根本沒有殺人。但無人採信。外婆對他哭喊:「你怎麼那麼傻。」他便不想再辯駁了,沒有必要。
沒上國中,他就到工廠做事。才剛離開父親那裏,他已經萬幸,有張床,有個不會打人的家。母親偶爾回來,只要聽見客廳的燈在深深的夜裡啪噠亮起。文強就會搖搖他的肩膀,要他醒來,他們出去和母親見面。房間到客廳的路竟然比逃往竹林的路還要長。
他一直都覺得母親陌生得不像自己的母親。
母親疲憊,困倦,身體因為類固醇而臃腫。
他知道她正在學著怎麼和他們相處。他也是。
他們三人坐在圓桌前,只有他跟母親沒有話。誰也不會看誰。
但文強怎麼學得那麼快,馬上就會和母親聊起天來。
母親對他說過的話,他印象最深的只有:「謝謝你照顧你弟弟。」
他聽到後唰地站起來,椅子都翻倒。母親詫異地看著他,他也弄不懂為什麼當時要生氣。
他放下自己的肩膀,對自己說: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都過去了。室友對他說:「我奶奶也是在我進來就死了,你只要忍一忍,過沒幾年就什麼都忘記。」
他把關門的人給他的菸分了一支給室友。室友邊摳腳邊抽菸哼著歌。
他原本以為能因此出去,見不到最後一面,起碼送最後一程。
到了隔天,卻連菸也不再送。整個地方都當沒事發生,他僅僅一人,在這裡無足輕重。
水泥牆、鐵窗、腳鐐彼此碰撞的刺耳聲響、濃濁的呼吸聲、鼻炎、感染的上呼吸道、厚重的痰、滯悶的空氣裡微微蒸起的汗味和霉味。
他放下自己的肩膀,對自己說:都過去了。
再隔幾年,傳來了母親辭世的消息。
他已經沒有什麼情緒。木然地接過幾支菸。
從他二十四歲進去,到出來,四十二了。
第一次警察找他,他在工廠,才剛脫下手套拿了便當。其他人跑來圍觀,他木然地回答警察的問題:幾點人在哪?那裡有什麼?去那裡做什麼?他習慣獨處,一個人到餐廳吃晚餐,「你沒賺多少還一個人吃這麼貴?」就這樣的理由,他還是被帶走。
他在車上非常冷靜。知道自己是無辜的,一切都還好說。
他以為家人們起碼會問他:「是不是你。」
文強拉著他的衣角,他安撫文強:「哥哥很快就回來了。」
文強不安的臉在他心底留了印子,像被鑿空了的臉中心,所有表情都陷進去,關於未來的不安、迷惑、感傷與不捨,全都在那個深深的凹槽裡。他才驚覺原來,原來文強也是會為自己的日子打算的。
他瞇起眼睛才發現母親房裡的採光非常良好。
文強沒自己想像中的那麼愚笨。文強記得的事情說不定比他更清楚。
雖然文強只能寫,不會說。總是和鄰居的孩子們玩在一起。外婆有時責罵文強,他會讓外婆知道,自己怎麼樣都好,就是不要責怪弟弟──他只要繃起臉,外婆就會住口了。
也曾聽過外婆跟別人說這孩子越長越大,脾氣越來越硬。
他心想:脾氣怎麼能不硬。
十八年後,這一排平房已無人居住。外面圍起了網與鐵皮,預定拆建。
他把筆記本放到塑膠袋裡,看見一個相框上有文強像是參加舞團的照片。把自己化妝成一朵花,跟其他朋友合照。他不自覺笑了,這是在他進去後的事吧。也收進去,他拉開抽屜,一些陳舊的衣物,他買給文強的,母親買給文強的,李先生買給文強的。
外婆的舊衣。浴室裡還有十幾年前的沐浴乳款式。沒有用完的肥皂。野貓的糞。他在長出雜草的廚房裡看見一窩沒開演的小鼠,光禿禿的,彼此交疊著發出細小的尖叫聲。他走到母親的房間,老窗花與舊窗簾,外面的陽光過度曝曬,他瞇起眼睛才發現母親房裡的採光非常良好。原來這裡是這個模樣。搬來後的那幾年,他從來沒進過母親的房間,母親帶著李先生回家,李先生摸摸他跟文強的頭,讚許他對文強的用心。
他想:這也輪不到你說。
當他背著文強逃跑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哪裡。
文強總在他的背上靜靜地跟著喘息。
父親在遠方揮著他的雙臂,越來越遠,越來越小。
沒有人相信他什麼事也沒做。除了逃開。
將來的日子他不習慣用來揮霍,好不容易才有現在的收入。
開始工作的那一年,一個和他同年的女孩也跟他進同一間工廠。沒多久,就離開。他從旁聽到一些流言,說是女孩不自愛,說是女孩自找的,在他們這間幾乎都是男人的工廠。他所知的是,副廠長叫女孩進房。聽了那些之後,他拿鐵條往副廠長的腿打下去。
之後他換另一間廠,賺了的錢要給家裡,也要給那個斷腿的副廠長。雖然不值,但他還是忍了下來。該還的就要還。第二個廠的同事跟他關係不錯,但沒有人知道他有個學習障礙的弟弟,他一邊操作機器一邊想著以後怎麼照顧好弟弟,一間大屋,一台電視,熱了要有電風扇,可以的話娶一個老婆,跟她說:「這是我弟弟,請你對他跟對我一樣好。」他和同事出門吃飯玩樂,早早就回家,從來不喝酒,偶爾抽菸,當時大家都在簽大家樂,他也固定玩一點點,貪多沉迷,貪多誤事,將來的日子他不習慣用來揮霍,好不容易才有現在的收入,在他那麼小那麼小的時候,他總相信,等到有一天,他能自己找飯吃,他就能帶弟弟離開父親。
他才忍了下來。
他離開母親的房間。還以為自己聞到李先生身上古龍水的氣味。
他走回自己的房間,裡面卻一樣東西也沒留下。
像是不存在的:這幢屋裡從來就沒有這個人。
他愣了一下,再壓低帽沿,靜悄悄地像誤闖他人的屋內那樣,向後退了兩步,接著走出去。

夜空黑得他從來沒見過,星星明亮,偶爾有熱風。
出去的那天,認識的人、久待的開門的人、來來去去的新的一批室友為他喝采:終於能離開,總算可以走了,將來又是新的人生。「你自己要自愛,要自重。」他不想辯駁。他從來沒殺過人。但他放棄上訴。請律師的錢,都能讓他們買一幢更好的屋子。
李先生惋惜地對他說:「你真的不再努力一下嗎?再上訴,或直接承認,或許可以減刑。」
他搖搖頭。他只掛心文強,但他不願承認不是他的事情。
他還記得那樣的畫面:從廳堂裡傳來外婆的哭聲,母親沉重的呼吸聲,屋外看過去半室暗紅,李先生在屋外抽菸,文強靜靜地望著他,夜空黑得他從來沒見過,星星明亮,偶爾有熱風。鄰居也走了出來,彼此交談,細碎的話語在他的耳際,他一句都沒聽進去。
他出來後,做過幾份工。一份在舉牌、一份在發傳單,後來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在賣場裡推著嗡嗡嗡轉的打蠟機,夜裡賣場收了,女孩們與男孩們都走了,大家都下班了,保全在每一層樓巡,見到他,也都點點頭,或跟他寒暄兩句。休息時間一起在外頭耐著冷風或對著夜空抽根菸,「大哥以前做什麼的?」「坐牢的。」「噢……」保全驚訝地看著他,他自嘲地笑。
起碼他能承認不屬於他的待遇。因為那是事實。
他回過頭撥了撥神桌上厚厚的灰塵,兩手都髒,衣服也髒了。
一小時一百。不錯了,第一個月預支薪,他還能租間雅房,跟另外兩個做板模的一起用同一個浴室。混著泥土的牛仔褲常常把浴室弄髒,他也為他們打掃清理,再用一張紙貼在浴室門口:「入內前先脫髒衣褲」,寫字了才知道自己還會寫字。國小時他就一直想,該怎麼教文強識字,帶文強寫,一筆一劃地寫,文強很久很久才能學會。
直到更久以後,文強會寫:今天哥哥帶我出去玩。我開心。
他也開心。一個字或一句話都好。一本薄薄的筆記本文強可以寫上半年的事。
每一天都沒有浪費,他在工廠裡笑,同事以為他交女朋友。
他後退離開自己的房間,自己從來沒住過這裡。十八年來第一次忍住想哭,他回過頭撥了撥神桌上厚厚的灰塵,兩手都髒,衣服也髒了。
媽祖的臉和多年前一樣黑。
他幫商場的地板打蠟時,那麼明亮,和他想像的自己一樣。
進去後始終擔憂的事還是發生。該來的避不掉,該躲的躲不掉。去的時候他側臉回望自己的家屋,不能說多麼有歸屬感,但總是自己跟文強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幸運;既然不能早早歸來,那永別或許就會發生──他一直記得這樣離別的場景。他年輕時以為記得可以寬慰他的日子,等他到了這個年紀,歲數漸大,他漸漸明白忘不掉的始終都忘不掉,如同被陌生人借走的日子怎麼樣也拿不回來。
太陽艷麗地毀壞這裡,過度的曝曬還是會讓物事在繁盛中逐漸萎靡。
在通訊行認識一個四十歲的女人,兩個小孩,離過兩次婚,對他說:「你看起來很斯文。」第一次去吃完飯上賓館,他笑著對她說:「我坐過牢,十八年,重刑犯。」她不可置信地看著他:「怎麼可能,你看起來不像。」他苦澀地笑。女人還是有點驚訝地倒退,他從她縮起的肩膀看見恐懼,他不怪她。
後來兩人還是在一起半年,個性不合、收入不合就分了。打蠟一天能賺多少錢?他出入搭公車,都用走路,他回到自己的住處,一樣有霉味、一樣從牆沿就留下過度腐壞的氣息、一樣自地面冒出陣陣寒氣,他睡不慣床,就把棉被往地上鋪。他不開窗,這樣跟過去那裡一模一樣,空氣不對流,一開門就聞到向下沉的空氣。
他記得的那些畫面,並沒有為他帶來生活的平靜。
他想找到文強,很久很久才鼓起勇氣回去。
他踢開老家門前的磚,決定離去。太陽艷麗地毀壞這裡,過度的曝曬還是會讓物事在繁盛中逐漸萎靡。
出來的第一天,他曾打給家裡,「您撥的號碼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他掛上電話。
他還想聽聽文強的聲音。
三月二十二日,雨天。媽媽說哥哥犯罪了,不知道。
三月二十三日,雨天。外婆一直哭。
或許有過這樣的句子。他記不得了,他進去前的最後時光翻閱當時文強寫下的日記。裡頭也沒剩多少東西。他想聽聽文強的聲音,翻閱日記,最後斷在他進去後的幾個日子,文強就沉默,再也沒有聲音。
每一天,當他睡醒時,好像都還能聽到竹林裡他背著文強的跑步聲。
離開老家後,他猜測下次再來,這裡真的要被剷平。不過,剷不剷平意義都不大。他有些後悔當年的堅持,卻又矛盾地絞起了手指。承認不屬於他的,他就什麼都沒了。他每天都在猜測真正的犯人應該是什麼人、什麼長相、何種身世,十八年了,當時如果有小孩,現在也都大了。
自己早就是沒有房間的人了。
李先生有幫文強找到工作嗎。文強現在還好嗎。關於這些,他無從得知。
還是得回到被蠟洗過的地面,推著打蠟機,步履維艱,無意遠遊──他一直記得那樣的畫面:幾個人,幾句蹣跚的承諾,細微如星火的情感起伏──地面倒映賣場幾盞殘存的燈光,在長廊與長廊之間迴盪著他跟機器的聲音。除了自己以外的腳步聲都太過奢侈。
他回到他的日子裡,每一天,當他睡醒時,好像都還能聽到竹林裡他背著文強的跑步聲。
他們兄弟倆在風中喘息。
「睡著了嗎?」
「沒有。」
「會冷嗎?」
「不會。」
「餓不餓?」
「不餓。」
「想不想回去?」
「不想。」
「會不會怕?」
「不怕。」
記得我好不好?
好。
作者小傳―蕭鈞毅
1988年生,桃園人,逢甲大學中文系畢,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曾獲台北文學獎小說首獎、林榮三文學獎小說首獎等,作品入選《九歌104年小說選》,為電子書評刊物《秘密讀者》編輯同仁之一。做過些許零碎的工作,今年嘗試專心寫小說、書評與論文,但時間分配過於困難,還是容易把日子與書寫全都纏成亂糟糟的線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