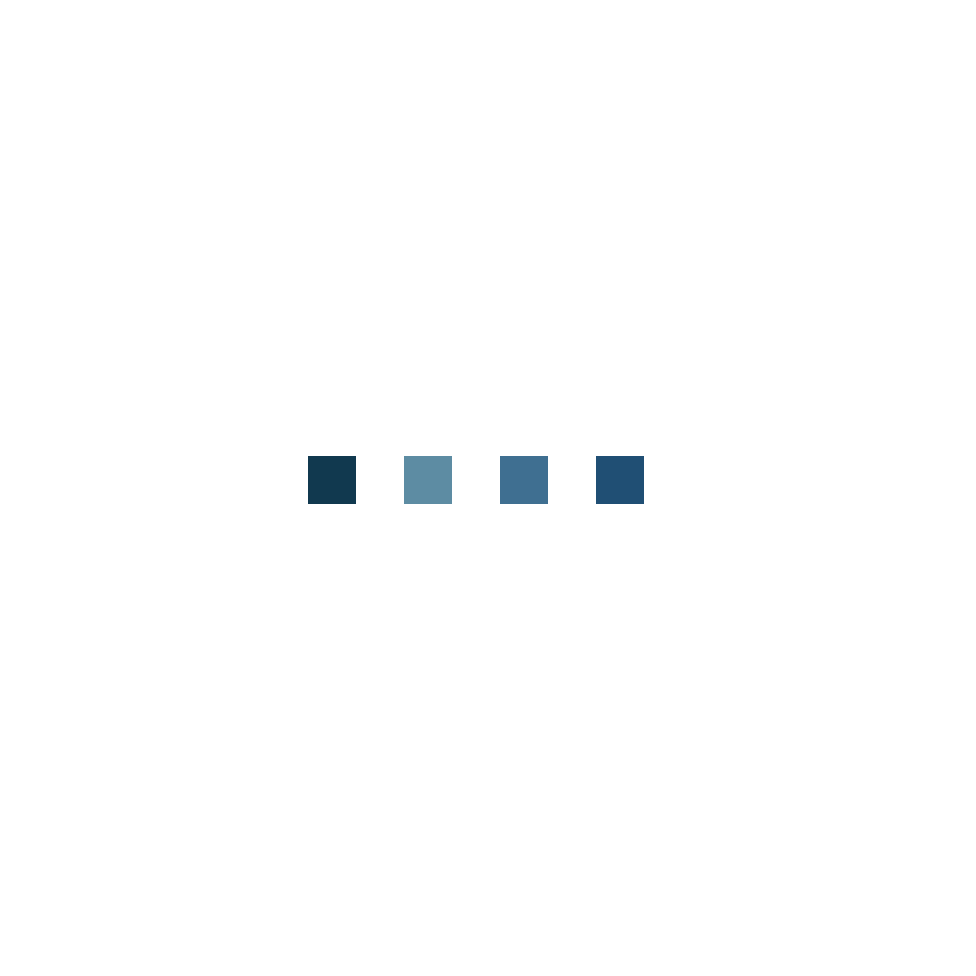陳栢青書評〈傷心辯證學──讀朱利安.拔恩斯《生命的測量》〉全文朗讀
「我們必須相愛,否則死亡。」這是詩人奧登〈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中著名詩句。等到詩集重印的時候,奧登自己又修改了這句話,「我們必須相愛,然後死亡」。從「否則」到「然後」,朱利安·拔恩斯在他自己的小說《10½章世界史》中描述了這件事情,以為這是詩壇最有名的修改之一。這修改的後續是,奧登索性把整句話都刪掉了,還修什麼,生命和死亡,全有或全無,乾脆都不要了。
《10½章世界史》是拔恩斯的代表作之一。寫於1989年,小說非常的奇怪,由諾亞方舟開始,裡頭一艘船接著一艘船,各式體例(書信、法庭答辯、小說、散文)連綿成長篇,把世界史順過一次,多豐富,多荒涼,但他還多出了1/2章,一個名為〈插曲〉的東西,那是什麼?在那裡,拔恩斯自己露臉了,「我來給你講講她的事情──」,〈插曲〉的第一行由此開始,很快你會讀出來,那是拔恩斯版本的《戀人絮語》,他寫給他熟睡的愛人,並發出種種提問,什麼是愛?愛使人幸福嗎?我愛你意味什麼?愛有益於生存嗎?小說家的愛很索然,在一本小說裡,明顯缺少了故事,都在提問,舉文獻,講典故,自問自答,卻有一種嚼勁。這些讀書人就是這樣,他愛的很硬,鮮少水份,藏的很深,很知識,有水平,大哉問,小心肝,你讀過,你會忘記,〈插曲〉是石板上的句子,是論文後面的註記,但我們的愛都在吃軟不吃硬,想起已枉然。

「我們必須相愛,□□死亡」,〈插曲〉裡談論了奧登的更動,其實是討論愛與死。當生命變成填充題。如果是你,□□該用哪個連接辭呢?「否則」?「然後」?「而且」?「從不」?你可以快速填滿格子,但要驗證答案,可能要花半生。至少,拔恩斯是如此。《10½章世界史》出版二十年後,世界終結了。愛人死去。當年一番春景春夢,愛的辯論喋喋不休,如今不堪問,哪堪提,那個永恆的□□,朱利安.拔恩斯以《生命的測量》來回答。
所有有字的東西,都可以是創作
好的作家帶你飛行,一開始你絕對看不出《生命的測量》要幹嘛。小說家有辦法如此,書分三章, 翻開小說第一頁,是19世紀還沒被佔領的天空挨擠著等待上升的熱氣球,人像攝影的大師納達爾有一只,皇家騎兵衛隊伯納比上校和知名女演員莎拉各有一只,它們按著章節依次升空,在不同的高度下體現為不同文體,是報導文學,還是小說?是論述?還是歸類為理性散文──這可以視為拔恩斯的正字標記,我們剛剛講過他的《10½章世界史》了,在他的創作中,透過各式體例的抽換,所有有字的東西,都可以是創作,一部小說往往變成「文字的奇觀」──納達爾上升是為了俯探,伯納比上校在高空看到愛情,莎拉找到自由,然後,氣球到了臨界點,外部壓力高於內部,球壁耐不住擠壓「砰」的──你忽然明白發生什麼事情,這就是這本書要帶你上去的地方,為了下墜。飛得有多高,墜得有多重。全書第三章,是拔恩斯自己登場了,他在墜落,「我的愛人死了」。一句話說死,或者,再拉長一點,「我們在一起三十年。相識時,我三十二歲,她死去時我六十二歲。」終於,〈插曲〉不是插曲,它成為尾聲,奧登句子中不是空白填空,只是默然。我們迎來了朱利安.拔恩斯創作生涯中最重的作品。
「將兩樣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世界就此改變。當下或許無人發現,但無所謂。世界終究是改變了。那是什麼?」每一個章節開端,總是熟悉的一句話,那說的是什麼?說的可不正就是所謂「愛」嗎?兩個陌生人的結合促成世界的改變。但另一個說法,霍華德‧蘇伯所著《電影的力量》中稱此為「異態混搭」:「把之前較少組合在一起也不被認為適合在一起的元素組合起來就叫做『異態混搭』,它會產生新的事物。」或者,史蒂芬金在《談寫作》一書中也提到「兩個原先沒有關連的概念突然凌空而降,使天地間突然有了新鮮事。」拔恩斯講出的,其實是所有創作者念茲在茲的創作真髓,所謂的創造,正是「將兩樣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但也許,他的答案就是這本書,《生命的測量》就是創作與愛的結合,而且不只是愛,還有更多,關於失去愛。
拔恩斯個人的生命大事件,卻也是倫敦的文學事件
這本書有幾種閱讀方式,一種是純粹文本式的,一種,是鏡週刊壹週刊式的,八卦一些把文本外的事情拉進來。其實是更理解書本背景。拔恩斯的妻子帕特卡瓦納(Pat Kavanagh)的離去當然是拔恩斯個人的生命大事件,卻也是倫敦的文學事件。帕特是倫敦著名的文學經紀人。他出身南非,大堆創作者對他的悼辭不約而同出現「feline」這個詞彙──「似貓的」──帕特也真是貓了(Pat可不就是寵物的意思嗎?據說他打給自己家作者會說「Pat called you.」和你叫寵物的語法剛好相反),他的顴骨優雅,眉骨連接到鼻子的輪廓線讓人想起貓的顏線,而他的行事也如貓般優雅。帕特演出過電影《Under Milk Wood》。直到60年代,他進入出版機構,成為文學經紀人。而生命中重要的轉折是1978年和拔恩斯相識。兩人在隔年結婚。那時拔恩斯正要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Metroland》。
帕特經手過幾個大咖。《正午的黑暗》作者Arthur Koestler稱她「我的小鯊魚」,他和拔恩斯喜歡在倫敦北部的家中招待朋友。晚餐時舉辦葡萄酒比賽,「整個倫敦的文學都聚集在他們家餐桌上」,《衛報》上的悼辭可謂是對文學經紀人的最高讚美,說起來他家也就像林海音家的客廳了。

拔恩斯對帕特的愛,看小說就知道,他曾用帕特的姓取筆名撰寫偵探小說,而〈插曲〉將他們的愛箝入世界史中。一個八卦是,1980年代帕特曾離開拔恩斯的身邊,和手下經紀的另一位作者發展出熾烈的戀情,那是誰?正是《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作者珍奈.溫特森,但兩個女生的感情終究沒能進入九零年代。「我為她寫過一本書,《The Passion》,那是獻給她的。」珍奈.溫特森在接受訪問時說。幾個小說家,幾本為他書寫的小說,為他創造與他所經歷過的,Pat Kavanagh的生命轟轟烈烈把文學家和文學界,小說的內面和外面連接起來。
為失去所愛產生痛苦,反而是愛她的證明
然後,是拔恩斯的《生命的測量》,拔恩斯寫出了傷心的極致,那是什麼,是怒,是尖銳,是刺,是茫然。看著他的自白與描述,小說家亂像你小時候會覺得怪的遠房阿伯。但其實是,小說家寫出悲傷的極致:「無效性」。事物的無效性。傷痛摧毀一切。一切被無效化。我們由此進入小說家的悼亡書寫之中。
傷心怎麼寫?過去書寫中已經有太多典範,還怕沒傷心事嗎?臨表泣涕不知所云,紙頁能哭出水來,當然也有「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這種,多不動聲色,庭中枇杷有多繁花盛茂,傷心就有多盛大。但拔恩斯的傷心書寫不同。如果拔恩斯的〈插曲〉是一種《戀人絮語》,他的《生命的測量》應該對應的就是羅蘭巴特的《哀悼日記》,巴特失去了媽媽,在《哀悼日記》中以短章的方式思索哀痛,拔恩斯則失去他的妻子,他們都是思考型的作家,用腦子傷心。舉個例吧,「只有在的痛苦中才能快樂」這是普魯斯特的句子,「我活在我的痛苦中而這使我快樂」、「我很痛苦。我無法忍受看到我的苦難被别人簡化」,這是巴特《哀悼日記》中的句子,「『大自然精準無比,失去有多寶貴,心就有多痛,所以應該也可以說人在享受痛苦吧!』我覺得這段話頗有撫慰作用,雖然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有享受痛苦的一天,但我也才剛開始而已。」而這則是拔恩斯。

你可以看到,三人成虎,而他們三人成苦,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傷痛下卻都在講痛苦與享受的關係,而且以思辨的方式進行,將最極端的概念放在一起,卻反變得理所當然,你瞧,為失去所愛產生痛苦,反而是愛她的證明,那不近乎享受,反而該說是快樂?這裡頭有一種悖論式的機巧,這些作家少用故事去渲染情緒,只討論概念本身,但別有一番天地,在文學史裡該自成一個系譜,這是傷心的辯證學。
愛人死去,我們該對誰生氣?
這純粹是腦子的事情。但這類書寫者從中逼出了心。他在辯論,是操作悖論,是自己在逼自己,當然,這類思考,很邏輯,似乎電腦也能做,電腦也能選土豆,可傷心辯證學不一樣就在這裡,例如拔恩斯提到,愛人死去,我們該對誰生氣?他自己列出種種可能的答案,氣死去的人?氣上帝?氣宇宙?氣這個世界?但拔恩斯說他都沒有,「宇宙只是做它該做的事情」,你看,拔恩斯的思考多合理,多理性,可說是思考的機械了。別人沒有錯,上帝沒有,宇宙沒有,世界也沒有。但他跟著話鋒一轉,好啊,大家都沒錯,「可既然這個世界不肯救她,我又何苦費心救這個世界?」沒有事物該為愛人的死負責是合理的,沒錯啊。但沒錯又怎樣,你們沒辦法救,我又幹嘛救你們,這讓我想到羅智成有詩「我心有所愛,不忍這世界頹敗」,拔恩斯則讓詩句顛倒了。這個顛倒,多自私,卻多深情,於理不合,其情可憫。
又或者,神話中奧菲斯明明被叮囑「離開冥府之前不能回看他的亡妻,否則妻子就會消失」,但他還是回頭了,這合理嗎?當然不合理啊,所以這才合理,「怎麼可能不呢?因為,雖然『沒有一個神智正常的人』會這麼做,但他在愛與傷慟與希望交迫下已然神智不清。你會在一瞥之間失去全世界?當然會了。這正是世界的用處:讓人在適切的情況下失去它。當尤麗迪絲的聲音在背後響起,有誰能遵守誓言呢?」你可以說,拔恩斯這本傷心書寫正是寫出這類「合理的不合理狀況」、「日常的異常狀態」,他不合理,但在傷心裡,一切合理,他異常,但這就是傷心的日常。
這不是因為愛。這是因為,失去愛。
此前一切,就都成了他傷心機器裡的零件

另一個《生命的測量》做到的奇蹟是,通常這類思辨性的論述,它會把一切拉遠。沒有故事,誰要看呢?那要怎麼讓人進去,讓人感覺到傷心。奇怪的是,拔恩斯偏偏做到把它拉近。他怎麼做到的?那就得依靠前面的章節,透過攝影大師納達爾、皇家騎兵衛隊伯納比上校和知名女演員莎拉,隨著他們各自上升的氣球,大氣未把你們拉遠,前頭他人的故事反而建立一個象徵與譬喻的平流層,一旦你讀過,你和拔恩斯看過同一個高度的景色,你們現在在同一個風壓之下了,此前一切,就都成了他傷心機器裡的零件。舉個例吧,「衝擊力道之大,使得他雙腿沒入花床深及膝蓋,體內臟器碎裂,迸散於地。」這是第一章描述氣球事故的情節,而到了第三章,當他寫到失愛後傷心處,便來上一句,「衝擊的力道更讓你體內臟器碎裂,迸散出體外!」熱氣球事故導致粉身碎骨竟變成了傷心的絕妙譬喻。因為你都先讀過了,前面章節不只是單純講故事而已,而是提供豐富的素材供後面章節使用,它們變成測量的公制單位,一如公分公釐公克公斤,而拔恩斯用它們讓你知道傷心的深度。
合理的不合理。日常的異常。拉遠的拉近。一片傷心不能解。在別人的血裡能暖自己嗎?但那不是問題,失去愛才是問題,你看到一個失愛的人,你看到一個誠實的人,你看到一個逼自己的人,你看到的,其實是生命的極境。那是我們有一天也必須臨經的地方,但誰能像拔恩斯那樣深入,而且坦承。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40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