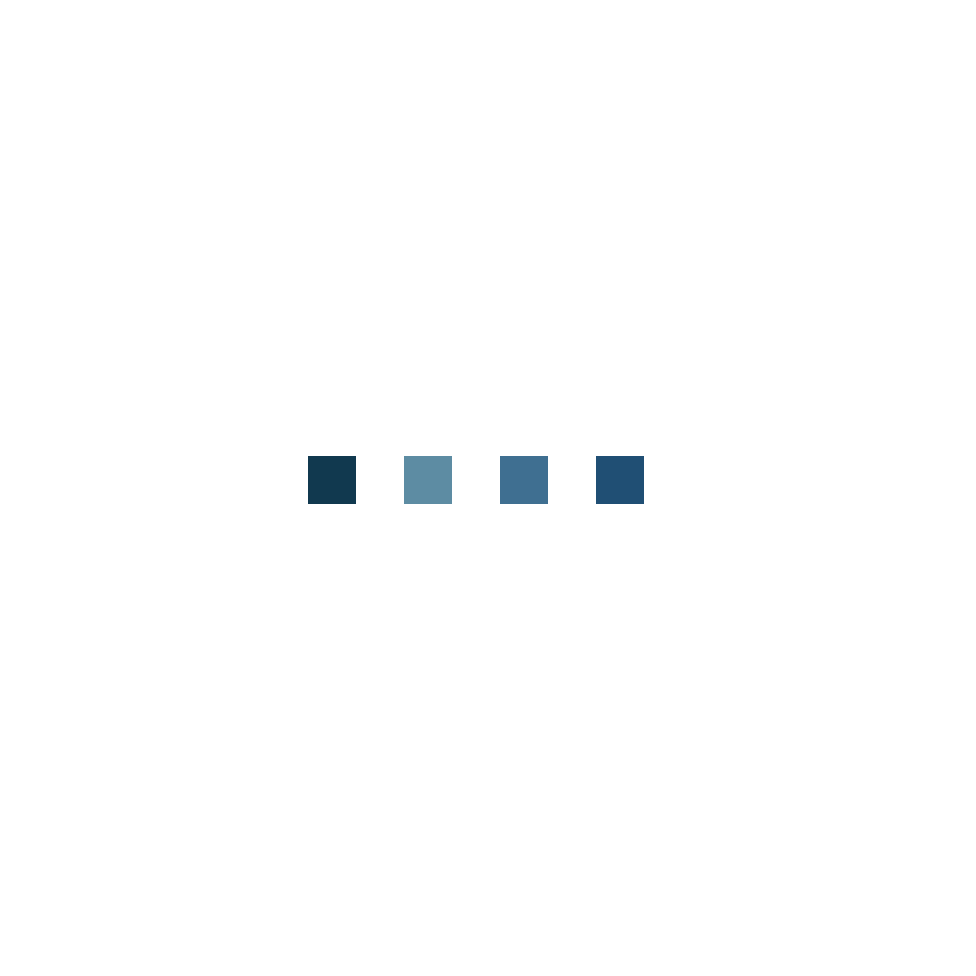徐振輔生態專欄〈雪豹III──蟲之草‧鳥之咒〉全文朗讀
蟲之草
父親說,他挖出一根蟲草時,會對山神說對不起,我把你藏下的寶貝拿走了。 ──阿來,《三隻蟲草》
將近六月了,高原的綠色像某種清晰的幻想,日復一日從易碎的乾草和雪塊底下漂浮起來。這時期要上山設置紅外線相機,應該儘量避免和當地牧民碰面。只是那天收完最遠處幾台相機後,我們都極為疲倦,所以當幾個藏族漢子從彼方晃著鋤刀直直走來時,我就愣愣地站在那裡了。
「你們幹什麼的?」其中一人丟出嚴肅而尖銳的問句。
「啊啊,我們沒有要挖東西──」我慌忙用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表示,我們是來做研究的。sà!我指向山頂說,sà!(雪豹藏文名為གསའ་,音同薩)。同時朋友拿出手機,播放一段稍早請寺院活佛預錄的短片:影片中,活佛盤腿而坐,以溫暖的聲音和富節奏感的安多藏語說,這些漢族人是做動物保護的,不會挖蟲草,請不要為難他們。
對方看完影片立即道歉說,不好意思啊,剛剛還以為你們是偷挖蟲草的。說完就往山下的白色帳棚走去了。
冬蟲夏草(特別指中華蟲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或許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藥材之一,產於青藏高原海拔3000到5000公尺的高寒草坡,五月到六月是最主要的採集季節。在這一、兩個月中,產區會進入一種很不尋常的狀態──城市荒涼空曠,人群湧向偏遠小鎮,公路嚴設關卡,山間帳棚林立,學校放長假,鄉政府大門深鎖空無一人。這時若想進山做任何工作,除了跟管轄該地的寺院聯繫外,還得預先向各級政府和公安單位通報(特別當你是一個台灣人的時候),才能取得相當有限的行動許可。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蟲草的商業價值只是一枚初燃的星火,和其他藥材沒有兩樣,透過一些資金規模不大的行商往來於牧區和縣城間進行買賣。那時承襲人民公社的制度,草原屬於集體所有,任何人都可以採挖。到了世紀之末,蟲草價格不停上漲,外來者逐漸增多,彷彿那枚閃閃發光的星火飄進了森林,從落葉堆中生長出火焰。直到黃金之名如野火肆虐,年年湧現數十萬瘋狂的流動人口時,政府開始設置管制人員進出的檢查哨,鄉級幹部都要離開辦公室,駐紮關卡日夜哨守。邊陲小鎮變得熱鬧非凡,旅館住滿外地商人,建立起西部藏區到東部城市的蟲草供應鏈。2012年蟲草價格攀天,最高級品一公斤甚至到達了台幣420萬元(單位重量的價格高於黃金的2倍)。
蟲草如金,使得藏區年年都會為此發生衝突。2005年,州政府發放超過4000張採集證允許N縣居民進入D縣採挖,以致D縣居民不滿,私設路障阻擋外人,最後導致了兩縣居民大量死傷的嚴重衝突。後來D縣有位村領導彷彿回憶起曾看過的無數抗日劇,以一種幻象式的哀傷說,N縣做的事情,簡直就和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侵略沒有兩樣。
在青藏高原最後的那段日子,我也在設卡駐守的地方待過幾天,認識了D縣一位鄉長。他見了面老愛對我說:「你是國民黨的吧!我是共產黨,嘿嘿。」記得一個百無聊賴的午後,吃過飯,他開車帶我們在附近小山谷閒晃,隨後停在一處看起來相當尋常,底下堆積了一些垃圾的草坡旁。「沒見過蟲草吧。」他興致高昂地說,前幾天特別叫人不要來這裡挖,就是想帶你們見識一下。
以往進入野地探索,每一類生物都有獨特的尋找方式,大腦必須建立起各種資訊處理模組,讓自己的意識和視野適應特定目標。那有點像是在久別的午夜,反覆演練和情人的相見似的。因為心只能真正放進一個人,因此若想發現隱密的葦草蘭,就必須錯過蜻蜓飛行的聲響。

我之前從未見過野生蟲草,大腦找不到一套合適的應用模組,很快就迷失在眼下雜亂的草葉之中。我只能模仿鄉長的樣子,像一尾覓食的巨蜥匍匐爬行,卻經常受騙於一些細枯枝或紅褐色草葉,如同輕信謊言。
但冬蟲夏草的賦名本身就是一則謊言。它既非昆蟲也不能算草,而是一種蛇形蟲草屬(Ophiocordyceps)真菌寄生於山蝠蛾屬(Thitarodes)幼蟲的混合體。這種蛾類幼蟲棲息在土壤中,取食草的根莖。夏末之時,幼蟲一旦受到四處飄散的孢子感染,菌絲開始蔓延,器官漸漸被消化,就會殭屍般爬行到接近地表處,以直立之姿安靜死去。等到來年初夏,一根細細的子實體就會從蟲的頭殼穿破而出──
是這個吧?我用手指輕觸眼前那根幾公分高的、略帶彈性的褐色事物,瞬間就確定那是我的第一根冬蟲夏草。我興奮呼喊,鄉長就拿著一把小鋤走過來──那時他已經挖到好幾根了。我接過鋤頭,高高舉起,用力打進和目標物有一根指頭距離的地方,再使勁一撬,蟲草附近的土壤就會鬆動。此時只要從土中捏住蟲體,輕輕搖晃就能拔出來,最後再將鬆動的土壤壓實就可以了。
這樣一根蟲草──依照今年的價格,或許可以賣到台幣150元。那天我只挖了三根蟲草,鄉長和南木卡都挖了十多根。易言之,這樣一個休閒似的午後,我們大概收入了5000元。而在蟲草的核心產區,有經驗的牧民一天甚至能挖一百多根,意味著一戶人家一季的收入可以超過一百萬。這項後起的產業於是強勁地推動了地方發展,偏遠小鎮建起樓房、道路、電力與網路,夜晚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越來越多牧民決定不再放牧,只仰賴那一、兩個月的收入生活。
然而牧業被遺棄的原因不只於此。藏區粗放的畜牧方式需要足夠完整的天然草場,但青藏高原冬季缺草的情況年復一年惡化,像所有後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一樣,從皮膚到心跳都無可挽回地衰老。於是新世紀之初,政府開始讓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四分之一人口(五到六萬人)以保護環境之名禁牧或休牧,從草原遷居到城鎮。這些在空間、文化、生活上與故鄉瞬間斷裂以致無所依歸的人,很大部分只靠政府的低額補助度日。這時興起的蟲草產業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它成為了國家生態移民政策免於失敗的關鍵。
但真菌是一種極不穩定的資源,你永遠無法預測下一年它們是否還會出現,那只能交給地形、氣溫、日光角度、水的路徑、風的流向,以及土地中微生物的經驗共同決定,而後價格又得交給陰晴難測的市場決定。很多牧民在蟲草如金的時期揮霍無度,又在蟲草匱乏的年度借錢生活,如同活在一部真實又虛妄的神話裡,命運和蟲草打了死結。

但冬蟲夏草到底有什麼用呢?1950年康寧漢(K. G. Cunningham)等人從蛹蟲草(Cordyceps militaris)中分離出一種蟲草素(cordycepin),後來的研究認為它具有抗腫瘤、抗病毒、抗菌的效果,民間因此常以「經科學證實」之名宣傳成冬蟲夏草的有效成分。諷刺的是,天然的冬蟲夏草其實不含這個成分──但這也並不重要,因為當冬蟲夏草隨著商品鏈來到旅行的末尾,貼上比產地高出許多的天價標籤,展示在大城市的精品店時,極少真的作為具有療效的藥材被消費,而是以一種名貴禮品之姿出售。
蟲草輕巧,易於保存,卻又極其昂貴。在中國的政治與商業場域中,被大量用來贈送給各方領導或合作者,以便確認或兌換某些物事。採集者或許並不清楚,蟲草已經成為一種符號,一種如詩的意象。有一群在空間與社會階層上離他們遙遠無比的人們,以此作為溝通社會關係的語言。他們透過情人秘語般交頭接耳所編織出來的神話之境,竟爾成為了讓那些不再放牧的藏人神魂顛倒的應許之地。
「但冬蟲夏草到底有什麼用呢?」我張開手掌,向南木卡展示自己僅有的三隻蟲草。「我也不知道,」他看了看,思考一下對我說:「人家說是治百病嘛。」
鳥之咒
工作站附近的山峰上,有一片紫色的雪層杜鵑。南木卡說,那些花盛開的時候,表示蟲草季差不多要結束了,而當一種鳥開始「咕滴,咕滴」地叫的時候,另一種紫色的花就會開(後來我知道那是一種非常美麗的原生種鳶尾)。

直到有次在山谷中聽見叫聲,我才知道他說的是大杜鵑(Cuculus canorus),就是所謂的布穀鳥。這種藏族人視為吉祥象徵的鳥,最讓生態學者印象深刻之處,就是他們為生存所必然進行的欺騙與傷害。大杜鵑不會自己築巢或育幼,而是以巢寄生(brood parasitism)的方式繁殖。當雌性大杜鵑找到葦鶯或其他小型雀鳥作為宿主,會先躲在隱密處,等親鳥離開時偷溜進去(也有研究認為他們的羽色擬態歐亞雀鷹,可以將親鳥趕走),叼走一顆宿主的卵,再產下一顆自己的卵,此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這個卵通常比宿主的卵更早孵化,剛出生時,雛鳥會將巢中其他的卵推出巢外,讓自己免於資源競爭,而宿主依然會將他視為自己的後代來撫育。
已經六月多了,我不確定自己究竟錯過了多少次雪豹。那天身心俱疲地下山時,我第一次見到大杜鵑,遠遠看起來很像一隻鴿子,在暗色黃昏中不停發出「布古──布古──」的叫聲。他獨自唱著單調的歌,渴望情人的同時,彷彿也在喚醒沉睡了一個冬季的寂寞鳶尾。
「你知不知道他們在叫什麼?」南木卡問我。我說可能是雄鳥在求偶吧,像是唱情歌那樣的。「哦?是哦。」他跟我說:「我們有一種說法是,這種鳥其實日日夜夜在對一塊木頭唸咒。只到找到那塊木頭,帶在身上就可以隱身。」他有點靦腆地笑了笑。「不過從來沒有人找到,聽說是不可能找到的。」
每個人或許都曾在童年的某些時刻,希望自己暫時隱身於這個世界。我們留戀那些彷彿可以逃避時光追擊的地方,譬如家中的閣樓、衣櫥、堆放雜物的小倉庫,商場的公共廁所,上學經過的小巷子,或是一條沒有人走的地下道。好像只要把自己藏起來,就可以躲開大人世界的一切似的(但那時又是那麼渴望長大啊)。

如果真有那樣一種隱身咒,能不能讓我暫時躲進自己的白日夢呢?能不能讓所有人都看不見我,動物聞不到我的氣息,在雪中漫步也不會留下足跡;雨水穿過我透明的眼睛滲進土壤,月光流經身體落入腳下那叢受傷的鳶尾花。如果此時和風一起漂到山頂,是不是就能看見一隻沉睡的雪豹,聽見他的夢與呼吸,觸摸到他柔軟的、令我為之神往的、世界上最美麗的白色毛皮呢?
(不可能的,南木卡如是說。)但那確實是不可能的,即便一無所知且一無所願,世界依然會千絲萬縷地將你拉回現實,讓你無能為力地成為這道渾沌風景的一處細節。如同時光從背後追擊而來,所有童年終將老去。
「說不定就只有雪豹找到了那塊木頭。」我跟南木卡說:「所以我才無論如何也看不到他。」
「哎呀,那是不可能的。」他以一種異常的自信說:「那是絕對找不到的啊。」

作者小傳─徐振輔
現就讀台大昆蟲學系,即將進入台大地理所。喜歡攝影、旅行、貓。夢想是拍攝野生的獨角鯨、雪豹、天堂鳥等,有些人以為是神話的生物。靈感敲門時,也寫小說或散文。最近比較專注的主題有婆羅洲、北極、西藏和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