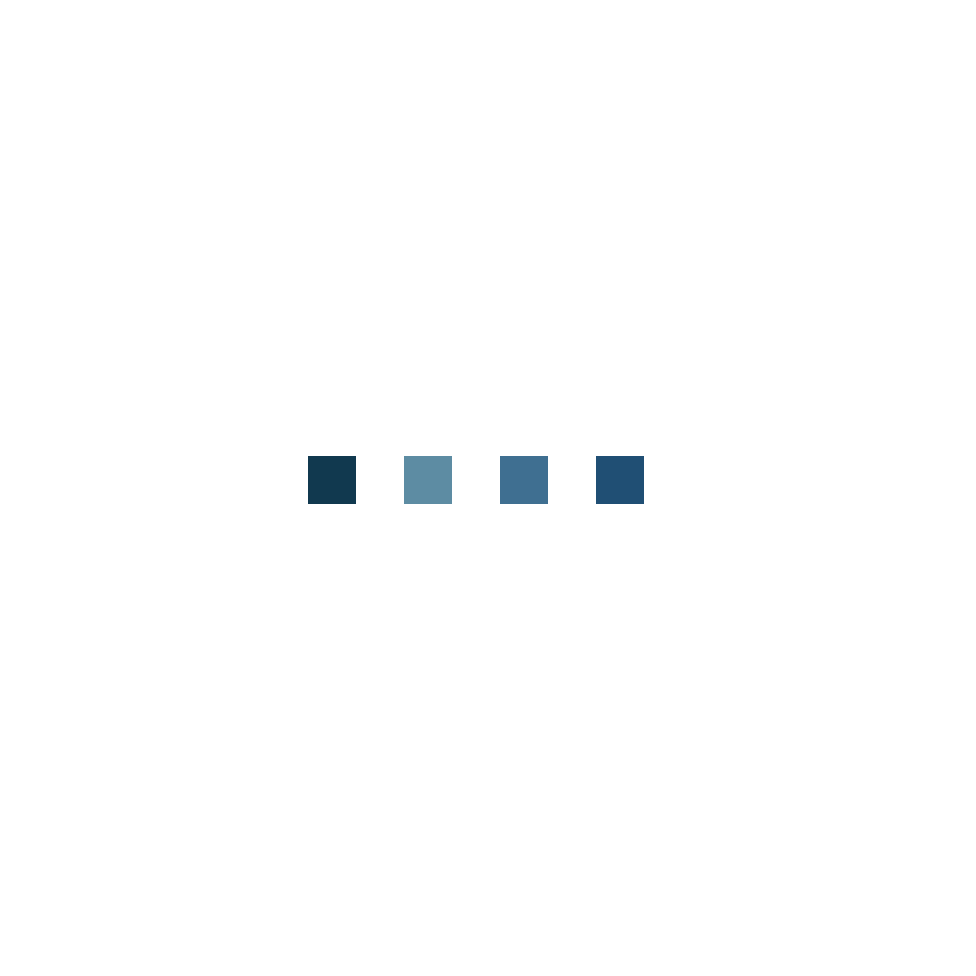黃麗群書評〈像《那個男人》這樣的,最討厭了——評《那個男人》〉全文朗讀
像《那個男人》這樣的小說,最討厭了,因為談起來讓人很為難,如果揭破故事的關鍵,將相當程度破壞讀者的興致,一如經常發生的慘劇,買來一本小說,從導讀開始讀起⋯⋯結果遭到強行谷阿莫,因此它的書封文案也只能半搔癢不搔癢、一切介於有說與沒有說之間:「一個虛構自己身分的人,是否有能力去愛別人呢?」如果不揭破,又難以伸手撫摸整本小說的情感核心。
然而換個角度看,《那個男人》的故事與這篇書評遭遇的窘境,倒可以說很相似:有一批絕對必須迴避的資料,然而這批資料彷彿是支撐其存在的一切意義。
到底哪個男人?

關於「那個男人」的事,大致如下:一個離婚後自橫濱攜子歸鄉、並繼承父母文具店的女子里枝,遇見來到小鎮從事伐木工作的外地男子谷口大佑,兩人再婚,感情甚篤,然而婚後三年餘,谷口大佑意外身亡,里枝聯絡夫家家屬後赫然發現:這個男人對妻子娓娓道來的身世是谷口大佑,這個男人的記憶是谷口大佑,這個男人的喜好甚至都是谷口大佑,但這人根本不是「所謂的」谷口大佑。里枝彷徨,求助於當年的離婚律師城戶,調查「這個男人」是誰。
有點像一則熟悉的辯證,確實,玫瑰若不叫玫瑰無損其芳香,但在這個故事裡我們卻相反地發現玫瑰竟不存在於玫瑰的香氣裡:一個人不妨像那個男人一樣拷貝身世,抄襲記憶,就算性情都在呼吸恍惚間相互浸蝕(但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這裡自然不好劇透),種種看似實在的來歷或本質在人身上竟都是虛的。那到底什麼是實的?是我們以為最表面也最不可靠的名字。
平野啟一郎寫妻子的震驚,不描述她痛哭,不描述她受騙,卻描述她坐在丈夫的遺照前內心無垠的荒涼:此後我在心裡該怎麼呼喚你呢?不能再叫你「大佑君」了,但我該怎麼呼喚你呢?
人只存在於他人的呼喚聲裡
據說在生理上一個人每隔七年全身的細胞就統統換新,宛如我們不能踏入同一條河流兩次,因此相較於「找出一個人的經歷與故事,卻找不到他的名字」,「找出一個人的名字,卻未必能知道什麼故事」竟然顯得更加踏實,與其說妻子想要知道「那個男人」真正的背景與來歷,不如說她更需要知道如何以正確聲響標記她失去的丈夫。好像《金枝》中曾提及東印度群島部族流行的風俗:一個人向陌生人自報名號是忌諱的,但允許由奴僕、同伴或者朋友代為告訴,也就是說,不管身體或心靈或記憶都不作為存在的證據。人竟是非常幻夢地存在於他人的呼喚聲裡。
但平野啟一郎的推進並不止步於此,在《那個男人》中,他將這本體論式的抽象辯證,以裡化表地與日本的社會議題結合,落實在故事裡的律師城戶身上,城戶是在日韓裔第三代,不曾在韓國生活過一日也無法聽說讀寫任何韓文,所謂韓國在他身上算是什麼?而高中才歸化、即使已是第三代仍讓人一眼就看出來「你是朝鮮人吧,看你的眼睛跟鼻子就知道」,所謂日本人在他身上又是什麼?城戶,三十八歲,無法回答。他娶了極為「標準」的日本太太,能夠明顯看出這個妻子在故事中是作為「整個日本社會」的化約而存在的,他與妻子微妙的關係,或也可解讀為作者謹慎的暗喻。而故事中數度提及關東大震災中的「朝鮮人虐殺事件」與日本近年的反韓浪潮,城戶有以日本人與殖民者身份謝罪的資格嗎?又有以韓國人與被殖民者身份聲討的資格嗎?這是一道出在他血裡的題目,但不容他回答,城戶也是日本社會裡的那個男人:一個不被日本人呼喚,也不被韓國人呼喚的人。
彷彿有些被小心翼翼掩蓋的真摯之物
舉重若輕是常見到快要貶值的讚美,但在寫的人都知道那確實是高難度的技術展現,《那個男人》在核心追索以外,織入的訊息量可謂豐富,例如婚姻親子、死刑存廢、法律與社群,儘管未必處處有最醒神的洞見,也不免有耽溺與自我重覆的時刻,但整體控場接楯都很高明,全書敘事的風格相對古典,沒有詭計與錯覺,沒有形式或時序的調度,穩健地線性推動,像剝開俄羅斯娃娃一樣,在正確的時機與正確的位置上出現謎、解開謎、出現謎、解開謎,令人聯想韓國學者李御寧寫《日本人的縮小意識》中「套匣鑲嵌」之一段。

李御寧舉石川啄木著名短歌〈東海與蟹〉中,大量反覆使用「の」的獨特語法為例,說明詩中從「東海」收縮到「螃蟹」再收縮到「淚一滴」,充滿將整個世界往中心一點壓縮的空間意識,或許也不妨以此理解《那個男人》的故事:在套匣般設謎與解謎的過程中,作者與讀者終於一點一點逼近所謂「人的自我」究竟該如何成立的內核,而那內核也確實像是「淚一滴」,一點也不堅固,無定向無定型,靠一點點點表面張力維繫不至吹散墜破。
有人說平野啟一郎是三島由紀夫再世,但不知為何他更讓我想起村上春樹,當然不只是因為他老是告訴你書中角色獨自喝了什麼樣的酒、聽了哪張爵士樂名盤⋯⋯而是在這樣一個充滿恐慌與暗角的故事裡,他的筆鋒不催逼張力,反而有種只是被懸念輕輕拉著衣角騰空而行的疲憊恍惚之感,這也是此書的魅力之一。而跟隨這樣半醉半搖晃的節奏,一路走到接近結尾之處,忽然有了如下一段中年危機男女的對話:
「愛上這個人包含他的過去。可是,如果知道了這個人的過去是別人的,那麼兩人之間的愛會該何去何從?」
「知道了以後,再重新愛就好了呀?愛不是愛一次就結束了,而是要在漫長的時間裡不斷地重新再愛吧?因為會發生很多事情。」
這麼芭樂,哪裡像三島由紀夫;這種芭樂,也不太接近村上春樹。問題是明明最厭煩「兩人之間的愛」一類辭彙與對話的我,讀到這裡,竟也忍不住有點惱火地承認:「可惡!被療癒到了。」明明是陰暗的秘密,疲憊的生命,荒涼的人身,既不開朗也不勤快,態度懶懶散散,有點裝模作樣,還一臉正經說些愛啊幸福啊的油腔滑調,然而在那中間,又彷彿有些被小心翼翼掩蓋的真摯之物……
本文作者─黃麗群
1979年生於台北,政治大學哲學系畢業。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金鼎獎等。散文作品連續七年入選台灣九歌年度散文選,另亦入選台灣飲食文選、九歌年度小說選等。著有散文集《背後歌》、《感覺有點奢侈的事》、《我與貍奴不出門》,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採訪傳記作品《寂境:看見郭英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