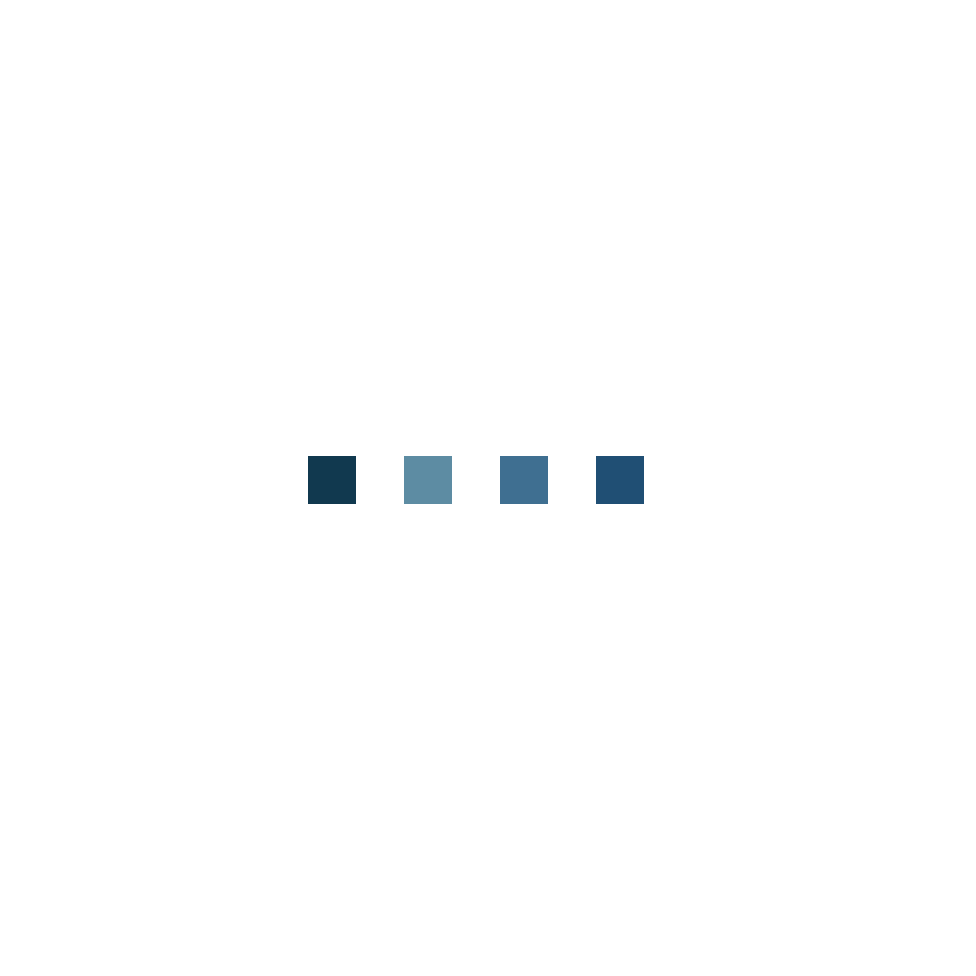在清晨便利商店寫作
寫小說對解昆樺而言也是這樣,把自己藏匿起來。他在中興大學教書,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到學校附近便利商店——一個明亮卻安靜的空間——寫作,寫到六點半回家練鋼琴,幫兩個小孩準備早餐,再送他們上學。日復一日,解昆樺說要努力活得每天都像重開機。
凌晨四點,開放又無人的便利商店,彷彿帶著寫作的玄祕,解昆樺在此花了快兩年寫《螯角頭》。連升等論文都在便利商店完成。為何是便利商店?「因為持續的孤獨對寫作者很重要。清晨的便利商店只有送報生與彷彿在守望的店員,但有時又可以看到各色各樣的人。有店員問我是做什麼的?我都回答出版業。」

便利商店適合寫小說,因為它十足入世卻又疏離。解昆樺說,寫詩是除法,需要不斷淬煉,最後誕生原鑽的鋒芒,但小說是乘法,必須有另一個人生跟作者相乘,「像我這樣的人生活很無聊,接觸不同層面的人很困難,所以在便利商店看眾生相。」
《螯角頭》裡,有夢想脫離黑道,卻身不由己的小嘍囉「螯仔」;被士林組合老大收養,繼承當家位置的原住民女子「顏希鳳」;前老大之子,仿若被罷黜王子,欲重掌勢力,試圖致希鳳於死地的「傅鑫野」:以及混跡黑道的警察「角利」。
看見五光十色的黑暗
四個人三組人馬在士林爭奪地盤。小說一開場,便是主角螯仔遇襲,在醫院醒來。解昆樺說,這是因為小說起源於一個異想:帶媽媽逃離醫院。
幾年前他母親生病住院,他每天從台中北上士林榮總照顧母親。「待在醫院,世界會縮得很小,窗簾一拉,更是小到讓人窒息,很想逃離。」他搭捷運經過士林站,想把在士林奔逃寫成小說。動念後,研究當地歷史跟士林夜市,發現那是五光十色的黑暗,遂成《螯角頭》。
五光十色的黑暗是什麼?解昆樺說,夜市參雜黑白兩道,都更更是士林難解的開發問題。小說最後,很難說誰贏了誰,只見「沒蓋好士林藝術文創商運中心,那鋼筋結構如何半空懸置,矗立於捷運旁天幕仍帶著深藍的士林市區,一如裸露骨骸的幽幽巨靈。」影射的便是遲遲未完工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小說裡這座裸露鋼筋骨骸的建築,確實像徘徊不去的幽靈,映襯每個人物再凶狠不過滄海一粟,剛強不過血肉之軀。解昆樺說,寫作要找最好的能指,都市空間就是最好的文本能指,「幾乎所有人都跟住有關,沒有人不回家,人與建築物的關係不只有家的溫暖,也可能是反差。」所以這鋼骨幽靈成為小說的詩眼,也像倒插的匕首。
解昆樺明明寫的是幫派,卻帶有江湖俠情,尤其是傅鑫野,像極了哈姆雷特王子。解昆樺說,反派傅鑫野是他用力最多的角色,「反派有深度,其他人物才會跟著立體起來。要說服讀者:這個大魔王值得主角去挑戰。」

讀太宰治的黑道二代
這孤獨的前王子、黑道老大,原型來自解昆樺以前遇到的學生。「他是我大學國文課的學生。平常他開賓士上學,一個人點一份披薩吃完,可以看出他跟其他同學都不熟。有一天,他對我講課提出不同意見,下課後我跟他聊了聊。漸漸熟了,他跟我說他祖父是做砂石業的,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整天抱怨無聊,經常來我研究室,我便推荐他看太宰治,沒想到他看得津津有味,說自己就像《人間失格》主角。結果他把我所有開的課都修完了。」
「也許他在文學裡找到了一樣的寂寞。」解昆樺說。
之所以用情寫黑道反派,也跟解昆樺的當兵經驗有關。2008年,他入伍當預官,本來指揮發射迫擊砲,因為害怕算錯角度跟路線,每天提心吊膽。有天看到心輔官在徵人,便憑著研究所修過心理學順利考取,因此在管訓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他們都有點破損,即使可能沒有自覺。」
讓解昆樺印象最深刻的,是來了一個十八歲新兵—滿身刺青,像恫嚇敵人的花紋,但怎樣都背不起來軍中口令,後來才坦承自己不識字。一問之下,他還成家有小孩;家中是陣頭,不想讓他父親養他的小孩,便在外面打工。然而不識字只能洗碗做外場,嫌賺得不夠多,就跑去販毒。「有天我看到他爸來看他,兩個人相對無言,默默抽菸。那種靜默像黑洞,把人吸進去。」

寫《螯角頭》,這便成為小說人物在育幼院長大的設定。「對很多道上人來說,友情比親情重要,不是因為沒有親人,而是親人可能像陌生人,無從靠近。」
寫小說走進歧路花園
人之間的關係怎樣計算才能得到適宜的距離,然而想靠近時卻又相斥。也許這就是解昆樺習慣在凌晨四點便利商店寫作的原因,在其中又不在。他說他喜歡「做個假人」,「《螯角頭》混雜對台北的印象跟想像。我喜歡這個虛構,讓我去演別人。詩追求真實,所以對我來說寫小說是享受虛構。楊牧寫詩有戲劇獨白體,就是戴上面具來寫虛。寫小說就像我扮成別人的時刻。」
裝作不是自己,走一遭陌生的路,活成新的樣子。台北出生的解昆樺,在台中住久了,每次到台北像走在東京。小巷彎道是城市無限延伸的血脈,在裡頭移動,人就小到成為細胞。解昆樺說,「我常常故意迷路,因為迷路很有趣。你嘗試離開不知道怎樣跑來的這裡,但有人在這裡住了一輩子。花一點時間路過別人的一輩子,不是很值得嗎?」
花兩年寫《螯角頭》,乍看好像詩人解昆樺岔了出去,非正道。但詩人也說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因為歧路有花園,會看到一座意義綿延的所指,映著日常之外的幽幽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