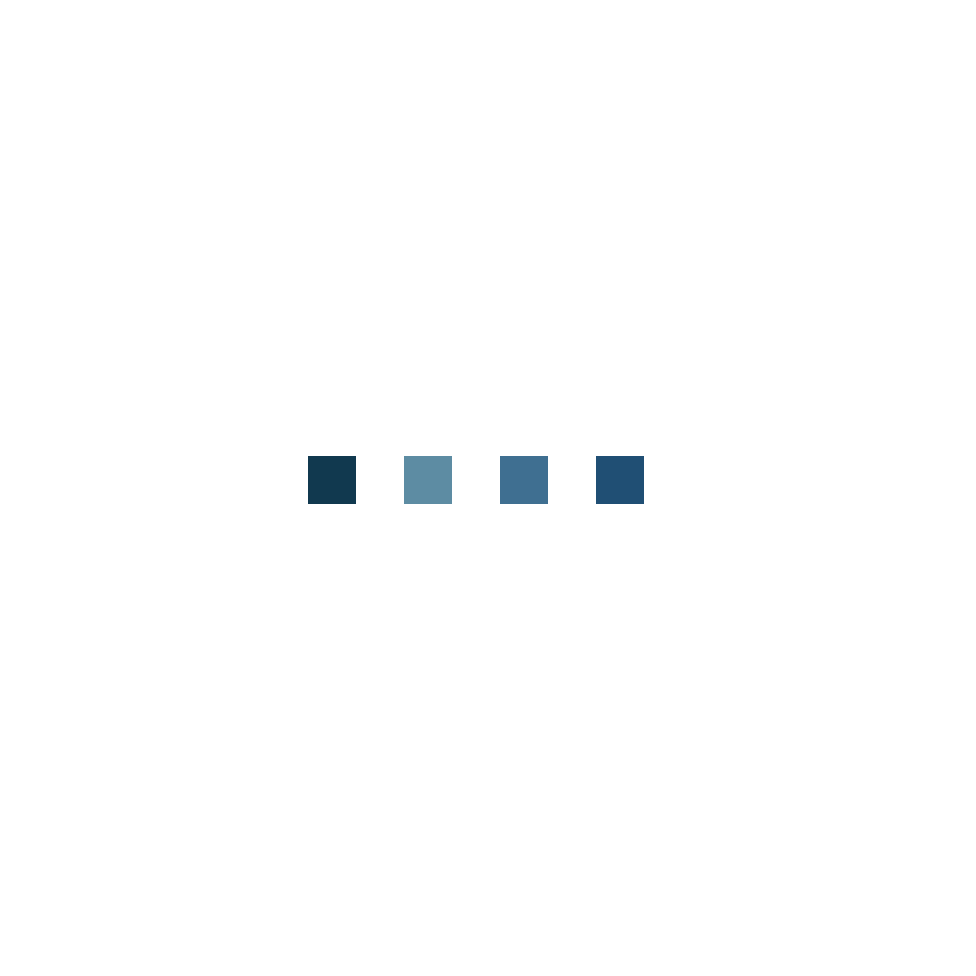徐振輔專欄〈放羊的日子〉全文朗讀
為了將一部關於西藏的、名為《馴羊記》的小說寫好,那年冬天,我確實在一個藏族朋友的牧場度過一段放羊的日子。
放羊的一天通常是這麼開始的。每天清晨日光撲面,朋友才合道會先起床燒水,貓咪趁機窩進棉被享受餘溫。由於外頭太冷,我不免賴床片刻,等四周暖和才勉強睜眼;接著翻身下炕,拿臉盆盛一些熱水刷牙洗臉。才合道給羊群餵完早晨第一頓草料,進屋還得餵我。他會弄兩碗酥油糌粑,擺一盤硬得像木頭的饃饃。「momo吃啊。」他說。我從來都不確定意思到底是「饃饃吃啊」還是「慢慢吃啊」,反正每天就是慢慢吃著饃饃。
十點左右,我便穿起藏袍,纏上頭巾,到外頭打開羊欄的柵門。
羊是來吃草的,光走路就沒意思了
才合道的牧場有兩百多頭羊,通常分成兩群:一群是產羔的母羊和小羊羔,具有最積極的生產意義,早晚能多吃兩頓青稞稈;第二群則是遊手好閒的公羊,待遇比較差,只能在山上自討草吃。此外還有幾頭自律又堅強的氂牛,一早放出去,傍晚自己回來,不用人管,也沒什麼天敵。
我被交代的工作是看管那群公羊,內容相對簡單,每天就是帶上相機、望遠鏡、筆記本和一條拋石繩,遵照指示將羊群呼嚕呼嚕趕出去。像我這種工讀性質的牧童有兩個基本功能:其一是讓覬覦羊群的獵食者忌憚,其二是指揮羊群移動。羊的性格傾向聚集與躲避,好像心底長著一株含羞草,因此趕羊的方法很簡單,你從一方靠近,牠們就往另一方滾走,像一隻巨大的軟軟的腳在踢一顆巨大的軟軟的皮球。這需要一點耐心和節奏感,如果放任不管,羊群會亂滾並散開,甚至分裂成幾個小群體。但也不能太急,羊是來吃草的,光走路就沒意思了。如果你發神經把羊球一腳踢飛,牠們會滾得很遠很遠才慢慢停下來,累的可是自己。所以基本原則就是維持穩定,秩序,秩序。
講得有點複雜,其實唯一的訣竅就是順著羊的步調走,牠們早已養成規律,知道自己什麼時間要幹些什麼。須留意的是,這個谷地由村裡幾戶人家共用,沒有釘圍籬,各自領域以山丘為界。有時移動路徑和他人重疊,最好小心錯開,以免羊群失控混在一起。雖然從屁股和角上的噴漆可以區別所屬牧戶,但仍會增添不少麻煩。
要想當個真正的牧羊人,至少得先學會辨別草種
放到差不多的位置後,我通常會找個地方睡一會兒,或者挖挖石頭、讀讀書、跑到山丘上收發手機訊息。這樣的閒散時光一天至少有六個小時,日子堅硬如石頭,讓人不知如何消磨。有時用望遠鏡看著山谷另一頭的禿鷲,看著看著就過去了好長時間。
「咕──嘎啦嘎啦!」當我這麼呼喊,脫隊太遠的羊隻就會咚咚咚咚回來歸隊。
如果只是這樣,就太小看放羊這回事了。
要想當個真正的牧羊人,至少得先學會辨別草種。從羊的角度來說,草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禾本科和莎草科為主的可口牧草,一類是像甘肅馬先蒿、黃毛棘豆、矮火絨草之類讓人討厭的毒雜草。作為羊群領導者,必須熟悉草場內的地形、溫度、風向、降水等環境因子,歸納植群結構的時空規律,藉此進行各種決策──首先按年齡、性別、生理狀態規劃羊群,決定每天使用的草區;在更大的時空尺度下,則要調整不同季節的轉場搬遷模式。如果這樣仍然不足,就得調度外部資源,也就是預判下一季的需求,考量出租或承租部分羊群和草場,和另一個精打細算的牧民協商契約內容,各自追求最佳生產效率。
從七千多年前馴化氂牛、三千多年前引入綿羊以來,牧業就逐漸成為青藏高原初級消費的主要力量。如果放牧過於密集,會導致植被高度和覆蓋度下降;反之若缺乏利用,也會讓牧草演替成矮灌叢。這兩者在羊的眼中都是荒蕪。一個好的牧羊人既是環境的聆聽者也是傾訴者,牲畜是溝通的語言,草原是複調的歌。你必須感知環境流變,隨時靈活回應。就像曖昧情人彼此試探心思那樣,無法躁進,也不能裹足,那是一種急於界定什麼就會立刻窒息的脆弱關係。
當領導長鞭一揮,人們就不得不在離家與返家之間徘徊
然而沒有任何關係是永恆的,半個多世紀前,西藏原有的社會結構迅速崩解,新秩序組織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單位管理牧場。彼時乘著革命風潮,不斷強調增產、增產、再增產。那些出身農業社會的掌權者深信,閒置土地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浪費,於是打著「牧民不吃虧心糧」的口號,大舉毀草種糧,結果造就一塊又一塊寸草不生的黑土灘。為了收拾集體化時期留下的殘局,一九八○年代後期,國家推動私有財產制,試圖透過劃定邊界、草畜分配到戶,解決生態學家哈汀警告過的公有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不過這系列土地政策依然沒有克服農業思維的盲點,反而繼續加強放牧的時空限制。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新興的生態焦慮在社會中蔓延,政府轉身就將草原荒漠化的罪責丟給牧民,指責他們缺乏先進環境知識,固守陳舊生產習慣,只想自私地擴大畜群。如此簡化地描繪敵人形象,對付的方法也就呼之欲出了──讓遊牧退出草原。
十多年來,中國持續推動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植草造林工程,同時將數以萬計的牧民遷出草原,送到如雨後蘑菇般四處林立的嶄新小鎮生活。我這趟旅程自西藏伊始,途經四川、甘肅、青海等地,經常在公路兩側見到整齊劃一的人工林,一旁掛上繼承革命遺緒的標語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能致富光榮,戴窮帽可恥」,儼然成為中國西北最典型的當代風景。才合道告訴我,這幾年很多鄰居的草場被國家收回去種樹,他們拿了補貼,就能進城展開新生活。「像我們這樣的最辛苦。」他不曉得是羨慕還是嫉妒,指著自己胸口說:「我六歲開始放羊,沒機會唸書,一輩子待在這裡,出不去了。」
然而不久前,我曾陪另一位藏族朋友去過所謂的牧民新村,那地方格局方正、秩序井然,但基礎建設停擺,形同廢墟。許多人儘管分配到新式房舍,依然選擇在牧區居留。當時朋友開車帶我過去,只是想拆些鐵鋁材回家用而已。
當領導長鞭一揮,人們就不得不在離家與返家之間徘徊,彷彿流離才是歸屬。
十點多,我們把屋內收拾乾淨就要睡了
平常到了下午五點左右,放羊鄰居們便會慢慢聚攏羊群,沿著同一條山谷歸返。羊蹄踢起沙塵,夕日下如一朵正在成形的雲。
這天回家時,才合道正蹲在門口為羊羔剝皮。許多新生羊羔沒能熬過寒冬,只留下一張皮子乾乾癟癟地晾在圍牆上頭。我進屋簡單梳洗,拿個臉盆,將糌粑摻水捏成小球,餵給剛分娩完的母羊吃。
晚上吃飯時,才合道神神秘秘地問我有沒有對象?我搖搖頭,他便用手機分享一張妹妹娜拉草穿著傳統藏服的照片,問我:「看看,漂不漂亮?」
不說客套話,無論誰來看,娜拉草都是個非常漂亮的人。
「給你要不要?」
「給我?」
「牧區很多姑娘都喜歡嫁漢族的呀。」
「是嗎?」
「對,漢族男人也喜歡嘛,從外地來看到漂亮的就帶走了。」他說:「然後換你給我找個台灣媳婦兒唄?」
我尷尬笑了笑,看著照片想說點什麼,想得太久,陷入了沉默。
「有人聊天就是好。」他收起手機,用筷子敲敲碗。「平常一個人,飯都吃不下。」
吃飽後,才合道繼續躺在炕上看電視,最近有部講東北話的連續劇,常讓他笑得吼吼作響。電視看完,他拾起一把四弦琴,自顧自彈唱了幾曲。十點多,我們把屋內收拾乾淨就要睡了。睡前他會打開櫥櫃上層的小神龕,看一眼毛澤東和達賴喇嘛的照片,呢喃幾句,關掉整天播放佛經的錄音機。待我上炕,他往火爐中添滿牛糞,便關了燈。
明天又是放羊的一天
床鋪很窄,我倆手臂挨著手臂。他的鼻息吹在耳邊又濕又熱,有股羊脂腥氣。
「兄弟,台灣在什麼地方?」
「很遠,在海的外面。」
「那邊工資咋樣?」
「六、七千吧。」
「包吃住嗎?」
「不包吃住。」
黑暗中的他頓了頓。「帶我去台灣行不行?」
「你想去打工?」但我知道藏民是很難申請護照的。
「我想去遠一點的地方。」
「如果能來的話,我會盡量幫你。」
「對對對,朋友就是互相幫忙。」他起身又拿手機,說想在朋友圈發我倆的合照,要我寫句話,啥都行。我拿過手機,想了想輸入:「帶台灣朋友回家過年。」他看了看,問我寫什麼?我說帶台灣朋友回家過年。
「嘿,這樣好。」他將手機擺一邊,躺回床上問我:「你以後還回不回來?」
我說會吧。
「來就聯繫我,下次給你宰羊!」
我說好。
「改天輪到我進城,青海也不待了,就跟你去台灣。」
我不敢說好,也不敢說不好。
「台灣也放羊嗎?」他問。
「沒有。」我說:「台灣已經沒有草原了。」
對一個熱帶海島的子民來說,要在空氣稀薄的高原熟睡其實非常困難。他安靜後,我試著不再胡思亂想,努力進入夢境,養足精神,明天又是放羊的一天。

作者小傳─徐振輔
台大昆蟲系畢業,現就讀地理系碩士班。喜歡攝影、旅行、貓。夢想是拍攝野生的獨角鯨、雪豹、天堂鳥等,有些人以為是神話的生物。最近比較用心的主題有婆羅洲、北極、西藏和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