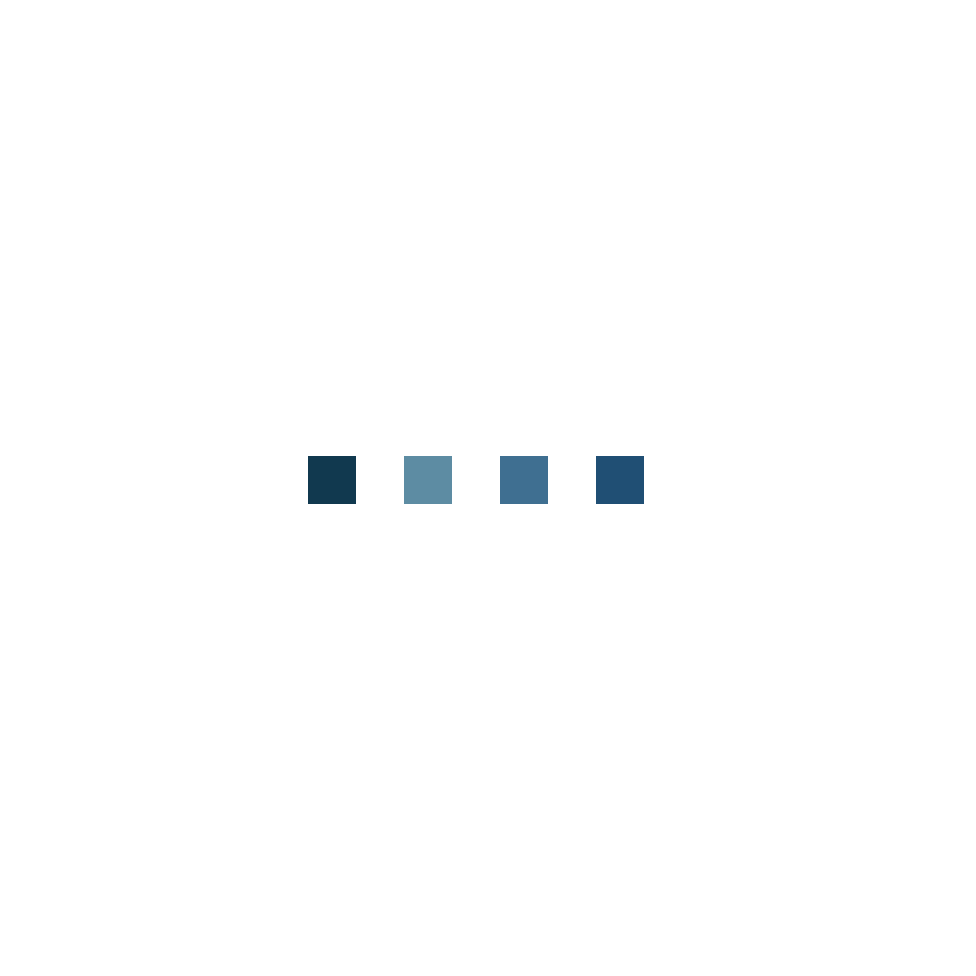金馬獎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也在記者會上表示,金馬獎不會以社會運動或政治因素來決定,端看影片內容、導演觀點、技法能否說服評審。
事實上,周冠威短期內很難離開香港。7月坎城影展發布展映訊息,為顧慮中國政府反應與導演人身安全,到最後一刻才公開。周冠威也沒有前往坎城,理由是:擔心去了就再也回不了香港,他要留在這片土地上。
有人說,如果香港是一艘下沉中的鐵達尼號,周冠威就是那位眾人逃竄之際站在原地,拉著小提琴,散播最後優雅樂音的人。
周冠威今年42歲,身材瘦長,臉蛋斯文,金屬框眼鏡下的眼神卻異常嚴肅執著。他6年前以《十年》中的〈自焚者〉打開知名度,影片預想2025年的香港:片中有2020年的港獨暴亂,迫使中共立國安法,支持港獨的青年歐陽健鋒成為第一個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入獄的人。在獄中絕食身亡,享年21歲,引發一個身分未明的自焚者。新聞事件投下震撼彈,陰謀論滿天飛,晚上市民到英國領事館前點起燭光禱告,同一時間年輕人衝進中聯辦縱火,中共引入軍隊壓制暴亂。2015年,有觀眾認為片中的警暴過於誇張,如今看來像智者預言,差別在於不需10年,4年後便已一一發生。
《十年》2016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然而周冠威的電影事業亦隨之自焚,沒有太多投資、演員願意跟他合作,生活陷入低潮。2020年周冠威好不容易憑《幻愛》從谷底爬出,光憑香港本土市場便有超過1,500萬港幣票房收入,而製作預算僅600萬港幣。

《時代革命》記錄這場沒有大台,沒有領袖的運動,從和理非的和平行動、勇武手足蒙面破壞物件、攻擊警察、民主派選舉,採訪對象盡可能全面覆蓋,包括示威者、記者何桂蘭、占中領袖戴耀廷、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等。他深知拿起攝影機拍攝反送中運動,無疑再次斷送了自己的電影前途。受訪時,他已刪除與本片有關的所有拷貝、檔案、資料、照片,因此他顯得很輕鬆,想說的話也已經透過電影說出,無須再說。一旦被捕,律師支援、家庭照顧已做好安排。
周冠威是虔誠的基督徒,信仰給他力量行公義、好憐憫,說這些如今《國安法》下少有人再敢說的事。鐵達尼號上小提琴手拉奏的那首歌曲〈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是感傷的告別,但周冠威轉為走入痛苦,與港人同行。
我們在金馬獎公布入圍結果前採訪周冠威,以下是他的訪談內容:
拍攝《時代革命》的整個過程,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公開導演的名字?很多人說會有被拘捕的風險,勸我匿名。有一個晚上禱告,我問耶穌:我很害怕、很恐懼,應不應該署名來承擔責任?那晚我夢見小學老師,他曾經讚賞過我,他說:『周冠威,你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我在夢裡感到應該要負責任。夢裡,我跟小學老師、老婆、小孩在一起,周圍有好多警察圍繞,虎視眈眈要調查我們,但我們很平安,那一刻我決定公開我的名字。
未公開名字之前,我的恐懼大概有5分,公開之後是2分

我小時候很自卑,因為我語言能力比較差,英文講不好,會被人笑,講廣東話以外的語言會很自卑。那個老師的稱讚對我來說是建立自信心的第一步。
第二天我接受訪問,訪問完記者給我一封信,是他太太寫的,說很喜歡我的電影,叫我加油,書籤上寫著林榮基的話「我盡我本分」,這又是一個巧合。我夢見多年不見的小學老師,又收到這個書籤,我就決定公開我的名字,對這部紀錄片負責任。
未公開名字之前,我的恐懼大概有5分,公開之後大概是2分。之前好像有個祕密,會令人恐懼;但公開之後,我若被跟蹤、恐嚇一定會說出來,沒那麼多祕密就會平安很多。再來,我手上已經沒有這部電影的材料,所有版權、資料運離香港,所以我一身輕。
有人問我坎城消息公布之後有沒有人跟蹤我?我都沒有特別回頭看有沒有人跟蹤,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不自由。我選擇留在香港,如果繼續想著會發生不好的事,活在恐懼中,這不是我追求的事,也不值得,坦然無懼就是自由。如果被拘捕,不就讓全世界的人明明白白知道我是一個政治犯?我不會擔心萬一坐牢無法發聲,因為我想講的已經透過電影、訪問講了很多,這部片沒有旁白,我給他們一個平台發聲,有些人跟我想法相同,有些人不相同,這都沒有關係。香港本應該有言論自由,這是《基本法》所保障的紀錄片拍攝。
很多人很難理解,甚至會說這樣對家庭不負責任,應該要匿名、離開香港,為了自己和家人安全多點考慮。但我的固執是來自信仰,我追求的不是個人的幸福,是公義、自由、愛,按《聖經》的教導才是對家人最負責任的作法,對小孩、太太最好的榜樣,不是移民去過幸福的生活。我27歲受洗,我的信仰是連死都不怕,會上天堂的!
太太很支持我的,她不會要我停止拍電影、賺點錢回來,從來沒說過。6歲的兒子很認同,我跟兒子說:「不論我坐不坐牢,耶穌都會保守我們。」他鼓勵我、叫我放心。我常帶他遊行,解釋給他聽,難過時也在他面前哭,擔心以後無法見面。但我很清楚,最重要的不是我的電影事業,不是我兒子、妻子,甚至不是我自己,最重要的是上帝那份愛。《時代革命》這部電影也是被神運用,若發生任何事情,我都會認為那是祂的計畫,被拘捕、更加危險的情況,我都願意。
當他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屏除所有的身分,不是父母的子女、學生、男朋友,已經是一個沒有姓名的抗爭者

我經常跟兒子講這些,這是對他的心理準備,萬一有事發生,他才能承受。我跟兒子解釋:原來在香港拍紀錄片記錄真實,警方、政府可能都會拘捕爸爸,因為他們不承認自己做錯。6歲的小孩看到警察打人,怎會不明白是非對錯?小朋友沒有那麼多立場,對就對,錯就錯,他們比成人更容易明白、接納,因為他們更單純。
我拍攝的一位示威者叫蛇仔,他說:當我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屏除所有的身分,不是父母的子女、學生、男朋友,當他走出來,就已經是一個沒有姓名的抗爭者。所有身分都不能高過公義、自由的價值,他說的話很打動我心,好像我內心最大價值的追求由他說出來了,甚至是喊出來的。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很年輕的學生,他在現場做勇武,都不是想打人,是想救人,幫忙一些來不及逃走的人。很多香港年輕人蒙著面,看起來很恐怖,但我知道他們除下面罩之後都很親切,不是全部,但很多都是這樣。
他還說,他不是很贊成「時代揀選了我們」這句話,是他們自己選擇走出來。我把這句話修改了一下,成為電影海報的口號:不是時代選擇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我跟被攝者之間有很大的信任,我不是只拍一、二次,是拍了好幾個月,做好幾次訪問。我會跟著不同前線的人,但不會干涉他們的決定,他們去哪裡抗爭我就跟著去。不同手足我都會見,請不同攝影師跟進,前後攝影師大約有十幾個。
手足蒙面,拍不到臉,也要拍到他們的心。所以我很重視訪問,很多勇武手足都做了起碼二次訪問,一次最少2個小時,有二個做了3次,加起來6個鐘頭的訪問。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勇氣,他們冒很大的風險那樣做,即使不認同他的行為,但他們的心我絕對認同,對美好願景、善良價值、對自由公義的追求。
有示威者曾經跟我說:「我為什麼給你拍?因為我希望被拘捕的時候可以被你拍到。」我心想:我不想拍到啊!他們認為,被攝影機拍其實也是保護,如果被捕那一刻有被拍到,法庭上有證據,比較不容易被誣告。很多手足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有攝影機拍,起碼可以讓人知道他們曾經存在,曾經做過這些事。其實這是很心酸的想法。我拍攝的受訪者,如今有人被捕,有人流亡到不同地方,我不敢太多聯絡,因為都有危險。
理大之後我很常做惡夢,夢到被警察打

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衝突我都在現場,我在理大二晚通宵,跟著一班示威者,也有不方便拍攝的時刻,因為他們情緒很激動,繼續拍攝不是很道義。有一次在理大飯堂,我一路拍攝的受訪者抱著我哭,說他出不去,也無法帶同伴出去,我也跟著他們一起哭,這個時候我無法拍,雖然紀錄片製作也許需要這些鏡頭,但我覺得有一個界線,人與人的關係可能比攝影紀錄更重要,他們需要一個出口,就找到我,我像局外人。他們不能跟其他同伴擁抱,因為擔心自己的的恐懼、痛苦傳染給其他人,這些時刻我就不會roll機了。
理大之後我很常做惡夢,夢到被警察打,有時候講起都會哭,但我希望不只是創傷,而是裡面產生出來的人性光輝我們可以感受到,成為以後的力量。
剪片的時候經常哭囉!看新聞的時候哭,祈禱的時候哭,聽音樂的時候哭,哭到我兒子都要笑:「爸爸你又哭啦?不要哭啦!」這是我面對這些際遇和壓力的反應,這樣比較健康。我在兒子、太太、合作夥伴面前都哭,有時候剪一剪,看著片段就哭,就停一停,哭一哭就好一點了,再回來繼續剪片。剪接剪了一年多,從2020年初到今年初,剪完做幾個月的後製、配樂,算是剪了很久,因為有很多footage,多到我忘了有幾個小時。
反送中運動已經沒人敢講了,傳媒也不報導,《蘋果日報》也沒了

在坎城影展放映《時代革命》之後,街上整天都會有人認出我,《十年》的時候沒這麼嚴重,任何地方,尤其市區,都會有人認得我,都會跟我說支持、加油,還有人說自己也是手足。他覺得2019年已經沒人講了,好像一個祕密、一種罪在心裡,國安法之後不能講這個創傷,是第二次的創傷,香港傳媒也不敢報導,敢講的《蘋果日報》也沒了。但他看到我拍紀錄片,願意講,他很感動,好像這個祕密被講出來,他甚至懷疑2019年是否有發生過?好像是假的,心理很扭曲,甚至會質疑自己,付出這麼多原來沒有價值。但我拍出來之後,他覺得有感受到一點安慰,最起碼可以講、可以紀錄,如果這部片可以肯定大家的付出的話,我已經很安慰了。
你說是不是我很政治?我一直都不是很政治的人,我第一次參與七一遊行是2003年,我1979年出生,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很晚的,也不是每年七一都上街。2009年我們爭取2012年的普選,政府官員說要「循序漸進」,我心想:你又騙我?我已經忍了十幾年,忍到真的忍不住,就寫了《十年》〈自焚者〉的初稿,但一直都沒有資金拍。2015年,《十年》的監製邀請我,雨傘運動之後,我就想:怎麼表達為香港犧牲更多呢?最激烈抗爭的犧牲是自焚,不同國家、歷史都出現過,台灣也有,如果香港也出現的話會怎樣?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自焚,我只是問香港人,你願意為香港犧牲多少?這個問題,2019年這場運動,香港人已經回答了,很多人願意站出來了,那我呢?我是做導演的,很想為香港出一份力,起碼可以記錄這些人,就拿起攝影機去現場拍攝了。
拍完《十年》之後陷入低潮,最後只好借錢維生、非常痛苦
拍完《十年》之後,我確實沒有中國的市場了,好像自己放棄一樣,確實是事業上的低潮。《十年》之後我有兩個劇本在找資金,一個一直都找不到,預算1,000萬港幣,第二個劇本規模小一點,600萬港幣,關於香港教育制度、中學生升學壓力、自殺的問題,有一個投資者願意投資,等了我一年,但我找不到有知名度的演員,有知名度的演員有政治上的考慮,不願意跟我合作,最後答應的投資也撤走。這對我打擊很大,我當年推掉所有工作,專心籌備這部電影,最後只好借錢維生、非常痛苦,2015年到2019年的4年間,一路都拍不到戲。

香港也不是好的土壤,以香港本土為市場的電影超過一半都是賠錢的。最辛苦的時候也沒怎麼辦,就繼續寫劇本囉!這是我的本分,我不會放棄電影,也沒有才能做其他的工作。
我期待有些不會恐懼的人願意跟我合作
我目前在籌備一部愛情片,確實有一個投資者知道我拍《時代革命》就撤資了,不得不暫停,但我希望我可以找到投資者,用正常的邏輯投資。這是無法強求的,有些人會恐懼,我期待有些不會恐懼的人願意跟我合作。
《十年》之後隔了5年才有《幻愛》,《時代革命》之後,不知道要隔多久,我希望有另一部《幻愛》。電影導演承受這樣的壓力是不正常的,但現實就是這樣恐怖。《十年》的5位導演沒有什麼機會拍長片,歐文傑也移民,我也有接到電話叫我們離開,說《十年》的導演會有危險,但我沒理,至少到現在還沒事,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