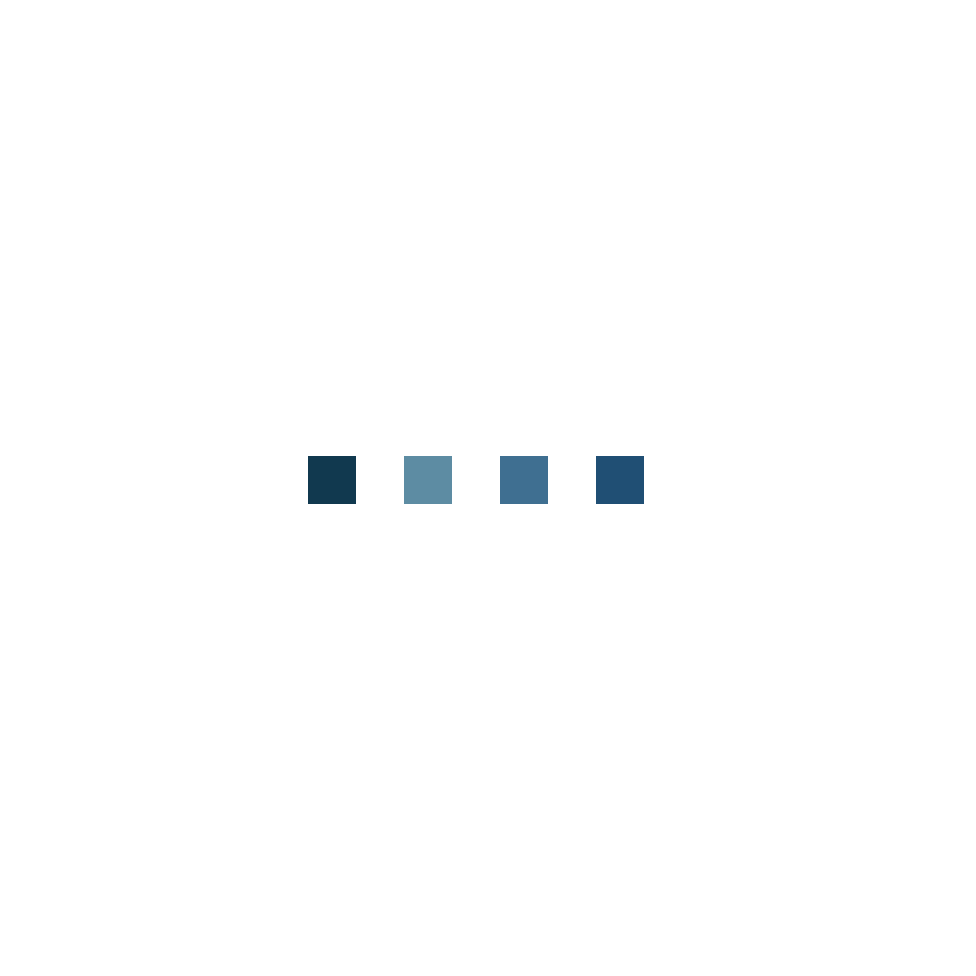那條溪流如靜止之玻璃,可能因那玻璃之厚度,使溪底布滿青苔的岩盤,呈現出一種「在另一個銀色光輝世界」的不真實感,似乎蟄伏在底部的它們隱隱有一種雄性動物肩背肌肉,壓抑屏息的動勢。導演和裸體攝影藝術家歡呼說,這裡夏天時太棒了,可以下水在那岩盤上漫游。確實因為這冬日寒流,包圍這狹窄溪谷四周,如夢似幻,像有個女神扯曳著薄紗的霧嵐,在青翠林木間忽而降下,忽又翔滾飄昇。但那股冷氣,似乎聚湊在這讓大家產生幻覺「已凍結」的絕美之溪。連稍上游50公尺處,主人花了心血找工人,壘堆了一道截住溪流的矮壩,那些每一枚都可以作一張石桌桌面、表面瑩潤且以灰色為主色調漸變淺紫、薄青、淡紅、暗橘,斑斕但又收斂的扁圓大卵石,壘排成恰好讓溪流貯蓄淹浸、清淺灑下的潔白水鍊。若非你聽見那迴蕩在溪谷間的嘩嘩沙沙水聲,會以為那也是靜止的。
這是最近網路上極流行的一句話:「整個世界被按下了暫停鍵。」

小溪主人非常自得自己在這一段攔溪卵石小壩花下的心血,那一枚一枚像巨人的圍棋子的美麗卵石,他們是從溪那一側(山區道路只有到那邊),架上滑輪,一顆近一噸重,讓工人這樣用纜繩運來這端,要在枯水期,然後在上游10公尺處先阻斷溪流,用大水管引到一旁,繞路過這一段,水從管子過,十幾個工人,照預先的設計圖,壘那些大卵石,砌上水泥,看上去自然天成,逸興遄飛,其實是非常嚴格的計量和工序。等要放水的那一刻,所有人屏住呼吸,看著那水位漸高,然後照他設計的,那麼優雅,像美人的長髮輕輕甩過衣領,那水不疾不徐,一種只是原地晃動的錯覺,淺淺漫過那堵卵石疊纍之梯,美不可言,當時眾人的歡呼,響徹這溪谷啊。
當然還有一些溪畔的工程,找怪手挖一個個坑,埋下一棵棵高大的日本黑松,他且將那帶著羽鱗般針葉序的粗幹,用繩縛綁,用木樁架撐,拉扯彎曲其造型。較內側則已植好一排筆直的落羽松。像魔法師降服且用鐵鍊鎖住十幾隻仍在掙扎、嘶吼的魔獸。事實上他已將這一切大尺寸的動態生物,造景進一幅巨大的宋人山水畫裡。
溪主人帶他們穿過一段「綠竹隧道」。這乍聽很老梗,但真的走進去,那是一種莖杆較細(可能是鳳尾竹),竹葉也纖巧嫋娜的竹,那「隧道」極窄,僅容一人鑽行,但超出預想的長,走進去後約穿行幾分才復鑽出,於是形成一種夢境的切換,當足夠長的時間,將外面的現實感截斷,在這青竹搖曳,竹葉垂灑撩亂形成的錯幻層次的「綠光」裡,奇特的《去年在馬倫巴》的電影夢幻感便將你淹浸。
走出「綠竹隧道」,是一個莫內式的蓮花小湖,以及延伸到山壁仞石處一整片濕潤、嫩綠,但又像秀拉點描畫法,那細碎光斑、無數翠綠、淺綠、暗橙、黃土赭,甚至有點點如小火焰閃燃的橙紅,那如上萬筆尖蘸著就那10種綠色系顏料,耐煩點捺、皴染成那麼大一幅,你不忍心踩踏上去的草原。
他從後伸手搭上那溪主人的後肩,說:「老哥,你實話說吧,這裡的每一莖草,是你花多長時間,從電氣窯中燒出來的?」
那溪主人咧嘴笑了。這可是最大的恭維。
主要是,他們一行人稍早前,在這「溪谷祕境」上方的入口處,參觀了溪主人(他是一位國際知名的陶藝家)陳列擺放在一間獨立展示屋裡,多年前獲得大獎的大型作品。就是一段約25公尺的廢棄鐵橋枕木。那其實就是如侯孝賢電影《戀戀風景》片頭,在十分、菁桐、猴硐這一帶山區舊昔煤礦的小火車行駛的窄鐵道,煤礦廢置了,可能某一段年久失修,靜置於無人知曉的幽谷中,濕雨浸蝕,荒煙蔓草,小粉蝶飛舞,而一塊一塊的枕木,原本那方形框角,被刨平的櫸木紋,如孔雀尾翼那斑斕圈紋的樹瘤,損朽腐壞、蟲蛀凹窟、裂口,或形成風頁狀纖維,或甚至一整截路基塌毀、或被燒黑成炭⋯⋯,這一切彌散著時間的哀感,人類工程棄置於大自然,那造化的雨淋風吹,說不出是寧靜或殘酷的崩壞。
但造成他們視覺、觸覺,以及大腦記憶區中資訊處理,產生了奇異的錯置、弔詭、迷惑,乃在於這一間展室中的這段,荒置於人煙稀少的山區,某一段壞棄的小鐵橋,或幽谷祕境中的某一段早已不通車的半世紀前的煤礦小火車軌道,那樣百感交集,枕木自身的木頭力勁,和大自然侵蝕的看不見的濕氣、熱脹冷縮、日曬、風颳,這種變形的扭力,枕木的韌皮部被削蝕、腐爛,但木質部如恐龍骨骼仍殘餘撐住那最後的形態。
所有這一切,卻是這位陶藝大師,用窯爐燒出來的,枕木的鳳羽紋、厚實感、不同角度的凹塌、顏色差異的變化,乃至那些彎曲拗折的枕木釘、崩碎的石基⋯⋯全部是窯爐中,「火的魔術」。
這真的不得不讓參觀者驚嘆不已,完全被那創造的魔性給震懾,那除了一種和造物者偷換概念,偷渡時間、風、自然與人工的狂妄,最可怕的還是在捏塑那些陶胚、濕泥,經過不知多少次試燒,以及雕刻時完全擬態木頭和陶的悖反,鬼斧神工於每處細節的腐朽木材的差參凹錯,但又要哄騙不可知的出爐後予人觀看之眼睛:這是整個在一生態中,大自然長時間的「編沙為繩」、「鑄風成形」。讓人驚嘆的是這創作者變態的耐性。他的手指、臉龐長時間挨近著窯爐的火,送進去一塊塊明明是陶塑卻要燒成栩栩如生的枕木,在更長時光中辯證生死的,另一種東西。N次方的失敗。這種意志太恐怖了。
之後他們在另一間展室,看到另一批更變態的作品:一整間我們那個年代國小或國中教室的木製課桌椅。一樣也是怪異、顛倒夢幻的木頭材質—而且是作為課室桌椅的橡木或櫸木這種硬木—一樣是整批木造物被置放於不知被人遺忘了多久,幾十年?上百年?的某處空間,召喚起經歷過民國5、60年代的這一輩人的集體少年記憶。每一張桌子的桌面,皆不同的磨蝕,細微凹槽,有鉛筆、原子筆油在上面亂刻、畫五子棋譜、寫哪個男生愛哪個女生不要臉、畫烏龜、畫小人,或有那個年代不知多少學生的外套袖口反覆摩擦形成的油亮感、包漿感,但也有桌面木材本身禁不起時間沙沙塌陷,破了一個何其自然的窟窿。也有木頭課椅崩解塌垮。這一切細微的重力,在這些排列成陣,昔日是島國反共、恐懼、物資貧乏年代,一個教室中集體「規訓與未來」的縮影。但人去樓空,只留這些時光徘徊的木頭課桌、木頭課椅。
而這幾十張木頭課桌椅,也是陶藝家一件一件從窯爐中,魔幻穿渡進現實的「火的魔術」。
如此可知,調戲地說這片溪谷,這片草原的每一莖夢幻不真的秀拉式點描綠光,那些小草其實是溪主人同時是這陶藝家用窯爐燒出的,其實並未逸出他狂想的可能性之外。
- 《大疫》新書正式上市,購書請點>>> https://reurl.cc/MNkb0K
- 《大疫》於鏡文學官網刊登,閱讀請點>>>https://bit.ly/3p2RG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