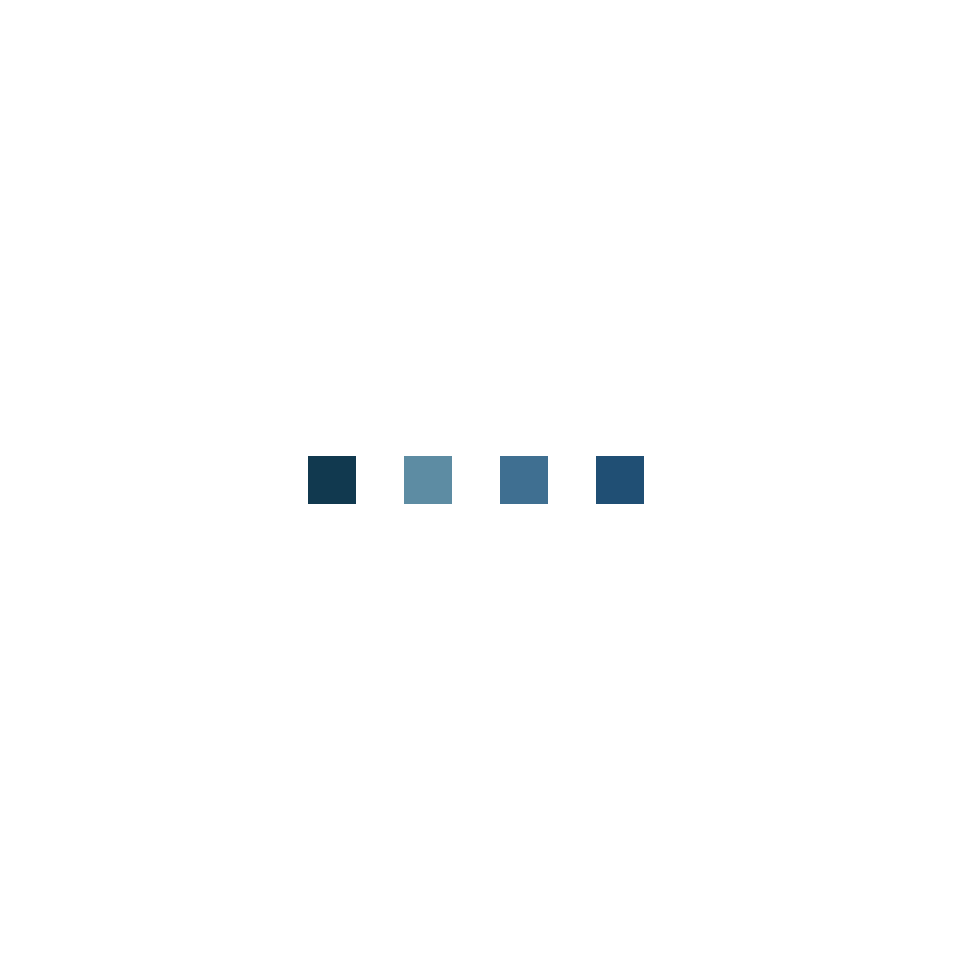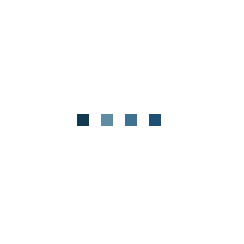黑是墨跡渲染黑,紅是朱砂紅。灰是是非不分暫且成灰,而白色恐怖。那是遊戲《返校》的基調,颱風之夜,河水變紅,世界成空,封閉的老舊校園裡,三年級學姊方芮欣一抬起頭,那個才遇見的二年級男孩魏仲廷已經吊掛於禮堂上頭,而早在世界隨著半空搖晃的視線顛倒旋轉之前,「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地下讀書會、思想檢查、密告、大拘捕……,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憑著個人意志能做出決定的年代,方芮欣始終找不到離開學校的路,「是忘記了,還是不想記得?」,記憶要不是昨日的鬼,留下來的我也許是過去的影子,甩不開的,不轉頭,也一直都在。

記憶的修改、掌權者的意志,大歷史裡小兒女、種種突梯亂錯、種種錯過與過錯, ……台灣人必然不會對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的短篇小說集《我們一無所有》(The Tsar of Love and Techno)中的情節感到陌生。小說建築於歷史之上,偏偏這頁歷史,本身就是小說。他可以被修改,被撕去。《我們一無所有》由專門從畫作中塗消各類反革命份子的畫家添上故事第一筆,塗消,去塗消革命行動那張畫裡黨的叛徒,他們當然不可能在畫中,他們此刻背叛了黨,怎麼可能過去參與革命?將叛徒的臉修改成史達林,「史達林當然在,他永遠都在,無所不在。」在與不在,時間在畫作裡外流逝,九篇短篇小說連作,也是「連坐」,裡頭人物再沒有關係,大時代之下,歷史的弔詭讓你們有關係,也就有了,黨要你沒關係,你又真的沒靠關係,那關係可大了。
記憶的力量,其實是遺忘的力量。
小說很憂傷,那到底是神的故事,還是神不在的故事。這麼痛苦的時候,神都在哪裡了呢?在被審判的時候,在讓士兵於夜暗「從床上猛然拉起」、「套上頭套」,在反抗軍和聯邦駁火暫停而「空氣裡的聲音像忽然被抽掉的午後」。小說很荒唐。那是人變成神的故事。人怎麼可以成為神呢?但就是有人控制一切,他審判。他制定。他讓人活著。他讓人死掉。他決定什麼是人,什麼不是。他要什麼都有了,於是什麼都沒有了。
馬拉是寫小說的能手。他深明小說的技術,小說的技術是什麼?且引小說家張大春的話說明,他以為小說作為一種記憶的藝術,其實是遺忘的藝術,「所以小說必須藉由人的遺忘本能來建立它的美學。怎麼講呢?比如說,我寫一個情節,放一堆細節在裡面,然後我寫一些別的,而讀者跟著我走了,就忘了前面。當我前面的細節,在後面再出現的時候,讀者會有一個快感:『噢,這個前面出來過。』」
所以電影《齊天大聖東遊記》裡,小混蛋至尊寶想要得到紫霞仙子手上的月光寶盒,他先去得到她的心,那段台詞遂成為九零年代告白的經典:「曾經有一份真誠的愛擺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沒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莫及,塵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電影進行九十分鐘後,至尊寶會真正愛上紫霞,當他戴上觀世音給的緊箍咒宣示從此放棄人世情愛糾纏前,同樣的台詞還會從同一張嘴中再被吐出一次:「……塵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如果可以給我機會再來一次的話,我會對這個女孩說我愛她,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觀眾必然會浮現那個念頭:「喔,這個前面出現過」,但同樣一句話,換個情境,所有人事已非的風景裡,他有了深度,笑話變成唏噓,胡鬧忽然太認真。讓人安靜到留下眼淚的,不是愛情,而是愛情的不可得。這是記憶的力量。其實是遺忘的力量。
馬拉的小說建築於這類的機巧。厲害的不僅在先聲奪人的「第一次」,更在如何啟動「第二次」。小說家總是能巧設伏線,而後讓它浮現。這「第二次」,有時是一首歌,有時是一張臉,有時是數字,或是共同的經驗,在這套技術啟動的瞬間,「窗外嚴霜皆倒飛」,至尊寶又遇上紫霞仙子,整個共和國都起了震動,那當然是計算,一種情節有效性的排列組合,但其威力不止於1+1,角色像被輸入了密碼渾身顫慄觳觫的瞬間,有什麼被啟動了,之於愛,之於背叛,之於恨,小說是抒情詩的高潮瞬間。
偶然與必然。巧合與計算。小說是這兩者的藝術。
但馬拉又不只是寫小說。
有些歷史恰恰是無法述說的,小說幫忙說了
他的小說背後,是活生生的歷史。而歷史是什麼?歷史正是偶然的必然。是巧合的計算。他的技術正好是歷史所要的(或歷史正好是他的技術所要的?),尤其是這樣一段歷史──黨要你記住什麼,什麼就成為歷史,黨要你遺忘什麼,什麼就不是歷史。而「什麼就不是歷史」這件事本身遂成為真正的歷史──歷史是記得,歷史是遺忘,小說操作記得,小說操作遺忘,歷史的聲音和小說的敘述在此重疊,那讓一切不只是藝,而近於道。
安東尼.馬拉是高超的工匠,但歷史讓一切成為畫布,他也就成為藝術家。他知道怎樣讓必然變成偶然。巧合其實是設計。人們遺忘一張臉,遺忘一句話,重新記起一張臉,記起一句話,這是小說。但當「哥哥出賣了弟弟,又親手把硬幣交給弟弟的妻子,要她親手『把照片上的弟弟都塗掉』」,為什麼一個人要另一個人強迫遺忘一張臉?這是歷史了。而「從此以後,他在所有經手的畫裡,偷偷畫上弟弟的臉」:十歲的弟弟、年幼跌倒的弟弟、結婚的弟弟、被帶走前的弟弟、如果中年發福的弟弟、如果安然老去了的弟弟……「在我經手審查的照片和畫作裡,在背景裡。在史達林和列寧的後方,在他們腦袋瓜後,在那裡,他們的眼睛找不到他」,為什麼一個人要把另一個人這麼明目張膽的藏起來,那到底是為了消除,還是為了記得?這也是歷史。而有些歷史恰恰是無法述說的,小說幫忙說了。
小說,且正因為是短篇小說集,那使得這套「記憶──遺忘」的技術有了加倍威力。當每一短篇畫下句點的同時,提供一種結束的幻覺。但各篇章人物卻又藏針縫似,出現在另一篇的某個角落,「噢,這個前面出來過。」,且不只出現,「原來他們是這樣的關係」,「記憶──遺忘」不只跨篇跨章,也跨時跨區,讓各篇章散成碎片,都是小小的悲劇,卻又合成高塔,「人類群星閃耀時」,時間終於讓一切癒合,時間就算沒有讓一切癒合,小說家也安排某種安慰──「你受過的苦,後人將不必再受」,小說在此真正發揮了他的力量,那是藝術的真實。技臻於道,技就是道。
當然,馬拉佔了便宜,歷史之荒謬,政治之無稽,集權者統治下的世界太違反人性,日常就是小說,紀錄片可能比劇情片更高潮起伏。那是小說的轉機,但也是小說的危機,問題不是小說可以多荒謬,而是小說僅只是荒謬:「你是否是賣弄一個奇觀?」、「別用別人的血暖自己」,且不說蘇維埃,看看此刻步調太快、「每天都有一點什麼被太新的社會甩落」的新中國,「我們的真實是太簡單的,太皮毛了。大陸有一個巨大的荒謬還沒被發現,那正是我們要去尋找的。這種真實和我們名之的『荒誕』是不同的,至少到目前,我還沒說我抓到了。我如果能真正抓到,才敢說,我在寫作上,發現全新的天地。我想發現最根本的真實。這是二十世紀重要的文學遺產。」這是閻連科所說,蘇維埃不遠,這個世界太新,記者都在寫小說,小說家每天則對新聞抄抄搞搞,但馬拉不一樣,我是說,為什麼不是歷史佔了馬拉的便宜?

因為他寫出歷史的裡面。「用背叛證明你的忠貞」,小說中畫家告訴自己的弟媳,只要出賣一個至親的人,去告密,黨就會相信你。像這樣的入黨,入族式,小說家前作《生命如不朽繁星》(A Constellation of Vital Phenomena: A Novel)也透過報馬仔出賣摯友寫過。那是黨所以能維持運作,令「我成為我們」的技術之一。
馬拉做了多少功課,他看得很透,是探底了,但又不只是告訴你「這有多荒謬」,他寫歷史的裡面,也寫他的前面,在集中收錄另一篇小說〈人民的殿堂〉中,蘇聯已經解體,小說主人翁在聖彼得堡打電話詐騙佛羅里達州的老太太,他假裝國稅局人員,開口不是證明我是誰,而是要老太太念出身分證後四碼證明自己是誰,「你得讓他覺得必須說服你相信他是誰,而不是由你說服他相信你是誰,這是訣竅所在」,黨已經不在,但那套務使「我成為我們」竅門都是一樣的,黨來硬的,詐騙者用軟的,背後是豪奪,是巧取,是利用人性的陰暗面,他知道你軟弱,他讓你自己屈服,重點都在於,「讓他必須說服你相信他是誰」,於是哥哥出賣了弟弟,於是老太太獻出了自己,只為了讓「我成為我們」。
「喔,這個前面出現過」,你未必然察覺出他們相似,但這就是在前面,時間的前面,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發生過了,而此刻依然發生,未來必然繼續發生。人本來就是善於遺忘的生物,記憶有什麼用呢?歷史就是小說,記憶其實就是遺忘,可就連遺忘也必須去記得,小說也點出歷史的一部分,甚至他就是歷史。馬拉不是在歷史的暗夜前放煙火,因為很黑,一點光,就讓你覺得亮了,出彩了。他讓你幾乎看見了全部,過去,現在,未來,但我們依然看不見全部,馬拉想揭露的是,那背後有一整個宇宙,那麼深邃,那樣孤單飄零,是沒有辦法通透的,而,人,這種存在啊……
本書作者安東尼.馬拉談《我們一無所有》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
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40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
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