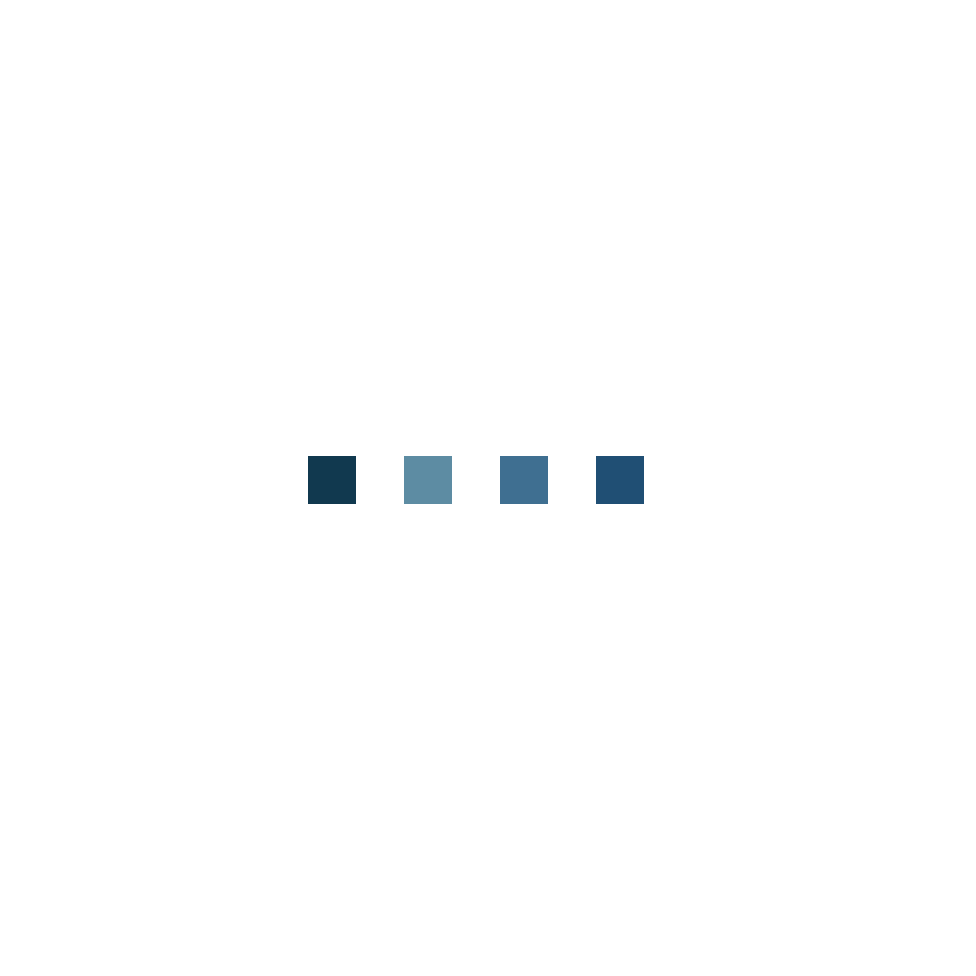2014年開始騎腳踏車是因緣際會,起初只因有個體育系的朋友想健身,找他一起加入。單車踩著踩著,他卻愛上了自由自在的感覺:「假如坐車,就沒有眼前這麼開闊的風景!」他開始渴望能走得更遠、看見更多地方。
網路打開了他的單車世界。他熱切搜尋許多這塊土地上遍尋不著的資訊──健身食譜、騎行裝備、安全須知等。眼前的一切,激起了他單騎天涯的憧憬,但這樣的夢想可能太昂貴。
那一頭送來的便宜貨
多數的以色列人,早在讀大學前就有長程背包旅行、飽覽十多國家的經驗。他們高中畢業後、在IDF服兵役兩三年後,通常父母體諒他們的辛苦,會贊助他們旅費到拉丁美洲或東南亞旅行。
但相較之下,在巴勒斯坦,自由旅行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巴勒斯坦縱使已有聯合國觀察員身分,但公民的國籍有如消失一般。除了少數擁有藍卡(世居在以色列1948年獲取的領土上,被轉為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外,任何人都無法擁有一本護照,也無法由以色列管控的機場進出。
他們唯一能做的,是跨越約旦邊境,申請約旦發給的護照,要價1000謝克爾(約新台幣8700元),只有2年期限。但這本護照與真正約旦公民的護照仍有不同,出國仍被視以巴勒斯坦人相待、被嚴密盤查;更弔詭的是,在某些國家(如與以色列交惡的黎巴嫩)卻又因以色列因素而被拒絕入境。
除了密不通風的政治因素外,近年愈形嚴重的經濟問題,也可能成為壓垮巴勒斯坦人的最後一根稻草。阿里畢業於巴勒斯坦最頂尖大學之一An Najah大學的行銷科系,但他對前途不樂觀。工作機會太少,許多學歷漂亮的電機工程、醫學系朋友,畢業後仍找無職缺,只能到餐廳當服務生、或到以色列以勞動換高薪。
阿里感嘆地說,由於經濟與不自由,巴勒斯坦幾乎已被以色列吃得死死牢牢,這比武力鎮壓還具有殺傷力。人們曾懷抱和平抗爭的希望,現已無望;激進的暴力抗爭,又會讓巴勒斯坦人被貼上更多負面標籤。人們正陷入一團僵局,大多只能安分守己地完成人生進行曲。
但阿里還抱著他的夢想。幾年前,他透過人在美國的親戚幫忙,申請上美國的大學就讀許可,但就在他帶著許可書翻牆到耶路撒冷、到美國大使館請求幫忙時,卻在面試這一關失敗了。「3分鐘的面試裡我只被問了些基本問題,例如會待多久、身上有多少錢,我不知道他們無法給我簽證的原因。」
騎車帶給阿里一點自由,但三年前,他還沒有一台自己的腳踏車。「有天我在學校,朋友問我要不要買一台自己的腳踏車?但我身上只有200謝克爾(約55美元)。他說:『沒問題,你就來吧!』」
朋友帶他到幾間特別便宜的二手店。與以色列一牆之隔的卡爾及利亞(Qalqilya)幾間狹小混亂的店面裡,塞滿來自以色列的二手貨。他看中一台黑色單車,有七段變速、平地爬坡綜合性能,才200謝克爾;TATONKA輕量化後背包才25謝克爾,安全帽15謝克爾。這些裝備性能良好,三年來伴他上山海,都還沒壞過。
他的大學所在地那不勒斯(Nablus)也有較零散的二手市集,「通常周六進貨,那時候血拼最棒了。」他找到20謝克爾的雙人防水帳篷、10謝克爾的睡袋,像挖到寶一般開心地抱回家。
「沒人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所以它們很便宜」,他苦笑著:「沒人理解這樣遊山玩水的樂趣。」他愈騎愈遠,跑遍西岸各地,找到一片草皮就紮營。手機裡幾乎都是自己與腳踏車的合照。有次他爬坡到離家3公里外的山區紮營,家人看他這麼雀躍,都覺得他瘋了,有家不回,去外頭露宿?
有時,他也騎車到抗爭現場聲援朋友,紮個營,在帳棚外插上巴勒斯坦旗。去年開始,他開始想要看看以色列這塊土地。
「騎車改變我好多想法,在這之前,我以為自己的人生也像多數巴勒斯坦人一樣:念個好大學、畢業、賺錢、買房子、娶老婆……。但現在我好想走得更遠。」
縱然危險,縱然孤單
去年起,他開始騎車闖關以色列,特拉維夫、海法、阿卡等幾個重要的城市及景點都遊歷過了,「沿海岸線騎,最平穩,騎得最舒服。」他窩在朋友工作的餐廳,免費吃最基本的Shakshuka和Hummus果腹。有時幫忙打打黑工,一天可領一兩百謝克爾,幫助自己繼續旅行。
但紮營是他最害怕的時間,為了躲警察、竊盜份子、不安好心者,他大多找較隱密孤絕的海灘紮營。幾年前他被警察抓過一次,最後被拷上手銬、押進車裡、載到邊境安檢站。凌晨沒有巴士回家,他在路邊的樹下睡一覺,直到隔天清晨。
有時,阿里騎得累了、或時間不夠,就想搭巴士放鬆一段。但幾個主要城市的公車總站都得經過層層安檢才得進入。他擔心自己又被抓包,於是靠google map查詢巴士路線、時間,等巴士駛離總站後才在路途中攔停。有時司機不開後車廂,他扛著單車到座位上,被清一色陌生的希伯來文包圍,內心忐忑不安。
這次是他第三次進入以色列,從家鄉Al Lubban出發,往南順時針繞一圈,走耶路撒冷、特拉維夫、海法……往北。
我和他約在Sea of Galilee見面,自己從更北邊戈蘭高地──另一塊全球爭議、以色列聲稱擁有主權的土地過來。
阿里騎到了我所住的社區,來電說對整片海景別墅的恢弘氣勢非常不習慣,害怕地催我趕快出門迎接。我問他為何害怕?巴勒斯坦明明也有這樣寬闊的景觀別墅;原來他說,常常遇到態度極不友善的以色列人,這樣的印象,在更高一層的經濟階級裡默默被放大了。
第一次看見舉世聞名的Sea of Galilee,他感動得歡呼,興奮地跳進一片藍水裡游泳。他要我幫他拍一張照,隨即把自己的腳踏車舉起來。
同遊一段的朋友原本也能看到這海景的,卻意外被憤怒的父親call回家了;他則繼續在路上,幾乎每一個小時,就接一通來自媽媽的電話。「有沒有吃東西?有沒有睡好覺?」「快回來,小麥收成需要你……」「會不會太危險了?回家吧……」全村的人議論紛紛,但這些都無法喚他回家。
他說,如果更多親友能夠懂得自己在做的事,「如果大家都能一起這樣走一趟,那該多好?」他點燃一根菸,述說自己的孤單。以色列一包基本款香菸10美元,每天抽半包,是他旅程中最花錢的物事。
夜晚,Sea of Galilee的湛藍轉為寧靜的黑色,向右望去有Tiberias燦爛的星火點點;望向左方,則是國界另一頭、水深火熱的敘利亞。徐徐的風與收音機裡傳來的英文歌曲,讓一切都像是不真實。
他打開臉書,和親友保持聯繫,又讀著自己密切追蹤的一位背包客遊記。
「網路教了我愈來愈多事,但也讓我傷心。因為它,我發現這世上好多美麗的事我無論如何都辦不到。」
作者:廖芸婕
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政大新聞系畢,前蘋果日報、報導者記者。跨國作品中,特關注自由、邊緣、理解、誤解、衝突、溝通、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