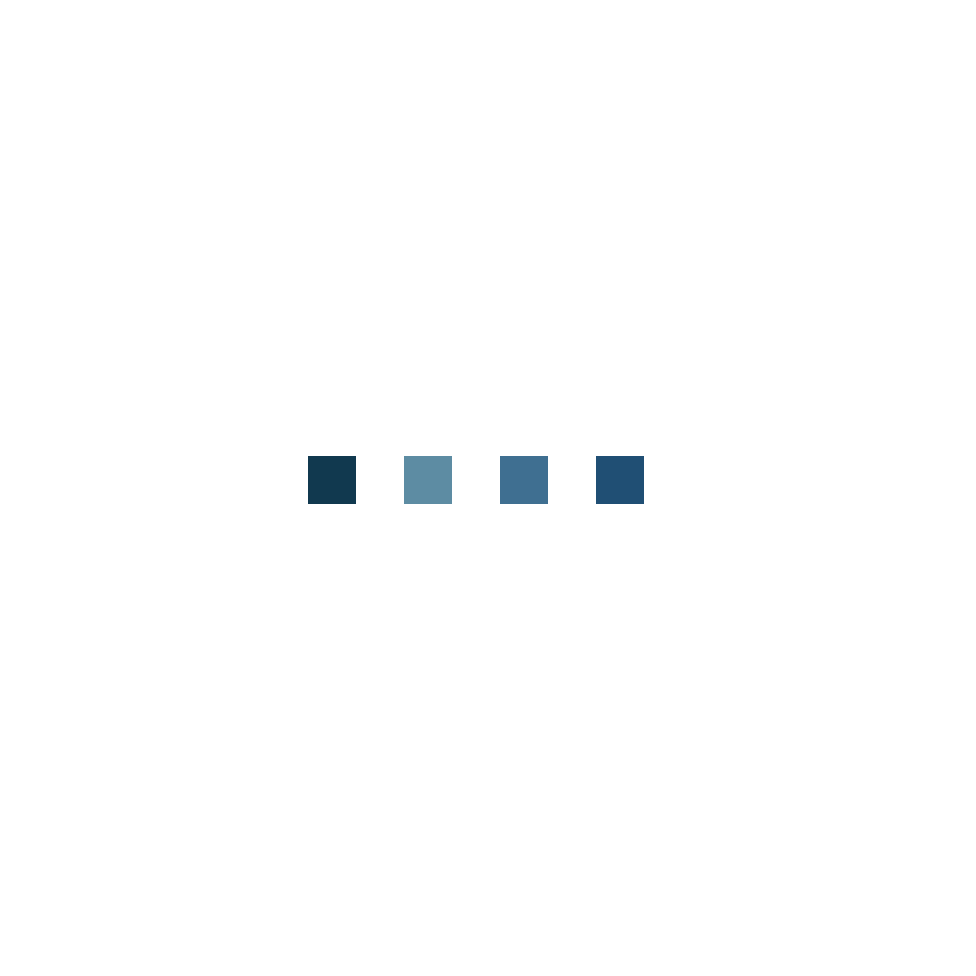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198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為台灣邁向多元平權的語言政治打開新的機會之窗。那是一場針對長期語言壓抑的集體回應,也是一代人為「能不能再開口說母語」而奮鬥的歷史時刻。若說那一階段的核心任務是「讓語言活下來」,那麼37年後,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其實已經不同:語言能不能被使用、被轉譯,進而被世界理解。
從「搶救語言」到「語言作為資源」
這意味著,母語運動正進入第二階段:不再只是保存語言,而是讓語言成為可流通、可再生產的文化資源。語言不只是一份需要被保護的歷史遺產,更是一種可以持續參與當代世界的文化能力。
第一個關鍵轉換,是從「保存型內容」走向「可使用的內容」。過去許多客語產製仍集中於紀錄、典藏與教學,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對國際與跨族群的閱聽眾而言,更重要的是:客語能不能談科幻、動漫、AI、半導體產業、加密貨幣、古典音樂或科技倫理?能不能講國際政治、移民、勞動、殖民與全球資本流動?能不能成為影集、Podcast、遊戲,甚至AI語音模型的一部分?
語言只有在被廣泛使用、被帶入新的語境時,才會真正「活著」,而非僅僅被保存。
不只是翻成英文,而是被世界理解
第二,台灣仍普遍欠缺「可被翻譯」的敘事包裝。走向世界並不是單純加上英文字幕,而是要能被放進國際文化理解的語彙框架中。當客家經驗能與「離散」、「族群語言」、「後殖民記憶」等全球共通議題對話時,客語才會被理解為一種世界經驗,而不只是地方文化的標本。
第三,跨族群、跨語言內容正是走向世界之前不可或缺的中介練習。透過原客語、台客語、華客語、英客語等混合型節目,客語不只是在「對外輸出」,而是在不斷學習如何被理解、被回應、被再詮釋。這種多語共存的實驗,本身就是全球化時代最重要的語言能力之一。
同時,這樣的內容形式也能開拓新的閱聽眾。當非客家觀眾不需要先具備特定族群身分,只要對議題與觀點感興趣,就能自然進入內容時,語言便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破圈」。
客語的未來,敢說也敢做
最後,不能忽視的是內容生產者的世代與角色。語言的未來,不只掌握在制度內的專業體系與政策支持中,也掌握在YouTuber、Podcaster、影像創作者、遊戲設計者,甚至迷因創作者手中。還我母語運動的下一步,或許不是再多一條語言保存的法律,而是多一批敢用客語說與做各式各樣的事情、並把它帶進日常與世界的人。
如果說37年前的問題是:「我們還能不能說自己的語言?」那麼今天真正該問的,或許是:「這個語言,能不能參與世界正在討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