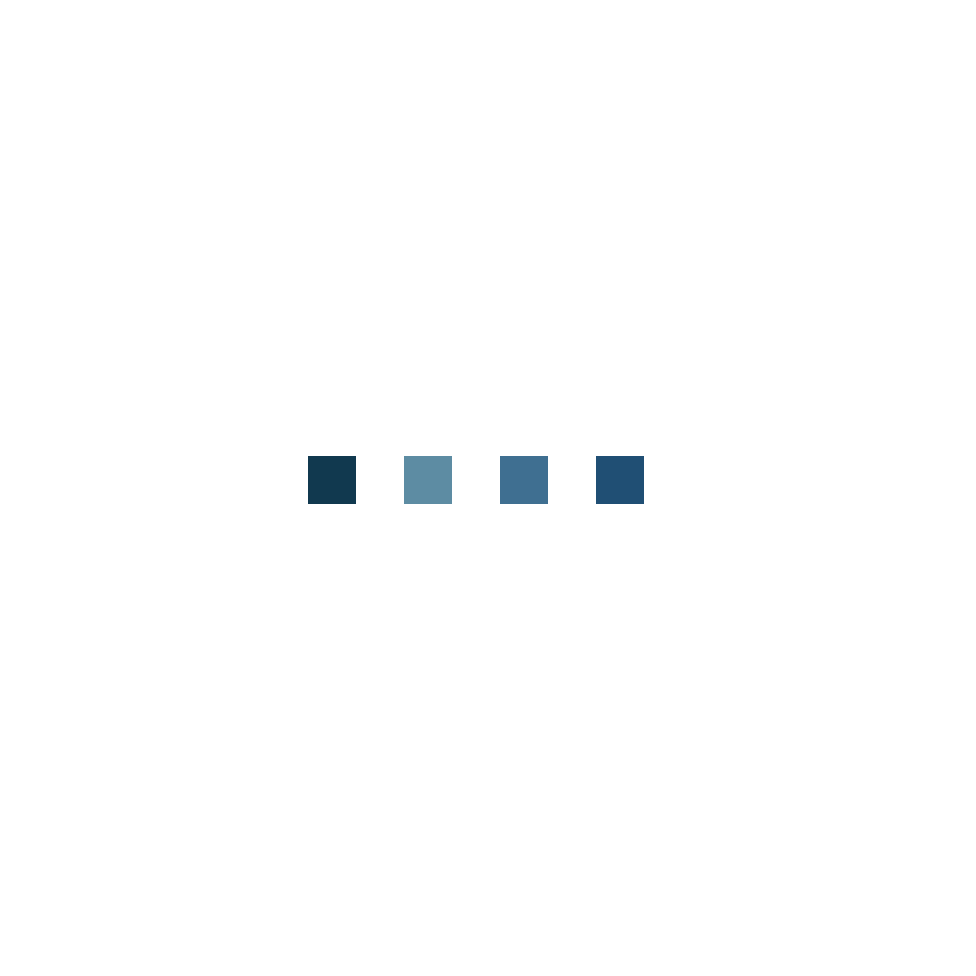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最近陸續在影展或院線首映的幾部客家電影實在精彩,其中一部是《丟包阿公到我家》。導演唐福睿延續其於《八尺門的辯護人》對在台移工處境的長期關懷,將鏡頭進一步推向更私人、也更難以言說的提問:那些長年在台灣照顧他人家庭的移工母親,她們自己被留在原鄉的家庭,如今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這部由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出資、與鏡文學共同製作的電影,今年10月曾入選2025年東京國際影展「世界焦點」(World Focus)單元的作品,正是在全球影展語境中,嘗試回答這個高度當代、卻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在我看來,《丟包阿公到我家》同時也是一部關於「客家如何重新學習定義家庭」的電影:當一位說著客語、逐漸失智的阿公,其日常照護必須仰賴一位說菲律賓語的看護工時,家庭不再只是血緣與語言的封閉共同體,而成為一個由跨國勞動、情感交換與倫理協商所共同撐起的生活現場。
《丟包阿公到我家》卻把鏡頭對準屏東高齡化客庄,以及長期被忽略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在地的老化與跨國的勞動,在同一個家庭輕喜劇裡面,笑著笑著,就撞見了這個社會正面臨的結構性的高齡化老人照護問題。
影片自然交織著客語、華語、閩南語、菲律賓語與英語。女主角菲律賓影后安潔兒·艾奎諾(Angel Aquino)在劇中同時說客語、菲律賓語與英語,被金馬獎執委會形容為「最大遺珠」,正好提醒我們:這些移工,不只是匿名的「外勞」,而是多語、多重身分的主體。
這同時也是一部關於「誰替誰翻譯」的電影。語言在片中不只是中性的溝通工具,而是嵌入照護體系中的權力與責任分配:孫子是否願意為看護阿姨翻譯成客語?醫療現場裡,又有誰願意替移工翻譯攸關生命的醫囑?這些看似微小的情節,實則不斷提醒我們——只要台灣仍是一個高度依賴外籍照護勞動的社會,多語平權與溝通權利就不應只是文化口號,而是必須被嚴肅對待的公共議題。
《丟包阿公到我家》近半場景在菲律賓拍攝。當我們習慣以「進軍國際」來衡量影展入選,卻很少認真想:其實台灣早就是一個被各種跨國勞動與情感拉扯的社會。這部電影,把台灣客庄與菲律賓呂宋島也同時放進世界的視野:不再只是觀光客式的凝視,而是勞動、性別、老化與語言政治的深沉交錯。
東京影展「世界焦點」單元這次選映帶有濃厚客家色彩的家庭輕喜劇,本身就是對「客家題材也是世界故事」的肯認。
如果說上一個世代的客家影像多半在追問「我是誰、從哪裡來」,那麼《丟包阿公到我家》所代表的,可能是下一個世代的提問:「我和這個世界因何相遇、要如何共同老去?」這個意味深長的問題,也在邀請所有的觀眾共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