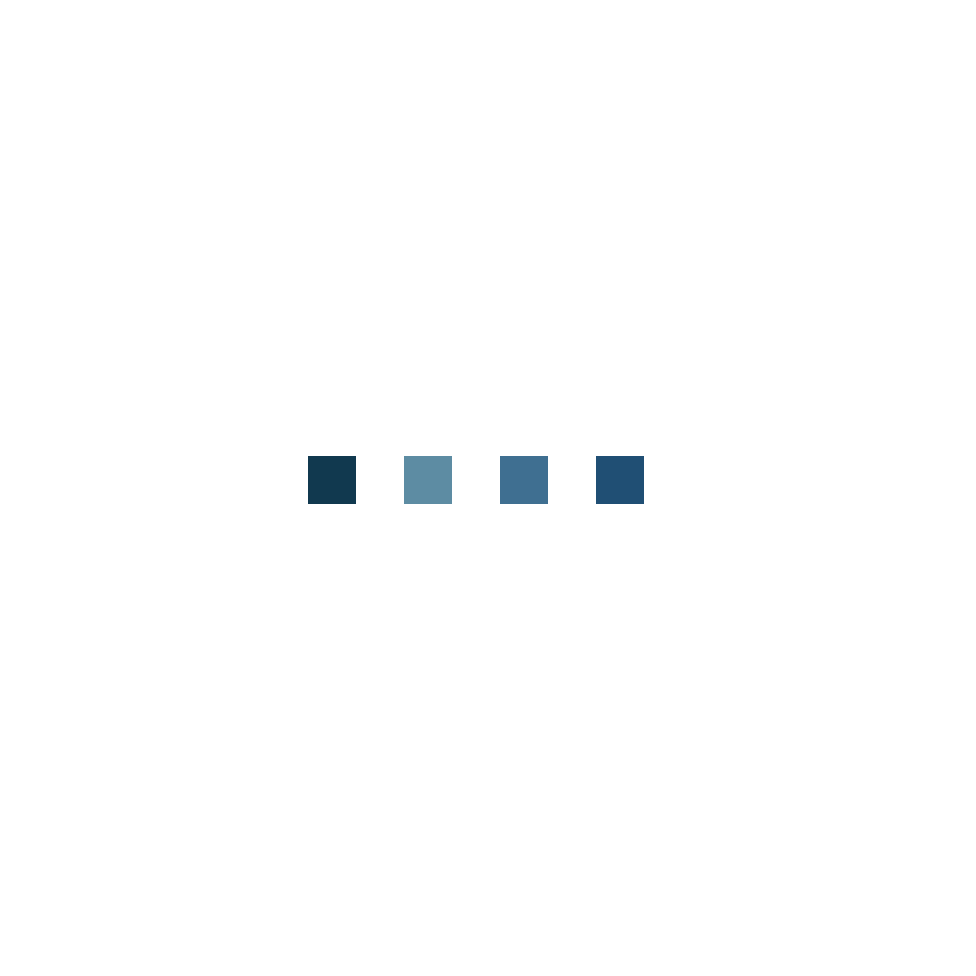我之所以會尋找並挖掘舒蘭街及其下河流,純然始自不服輸的好勝心,不服的是舒國治一口斷言,在今日台北城,是休想找到這條街這一泓河水的。
舒國治這麼寫著:「所有的台北斜路,指出早年的河跡。短如齊東街、寧安街,長如延吉街、安東街、舒蘭街、五常街等皆是。今之舒蘭街,在浩瀚大台北,根本不易找到,它只得一百多公尺。然當年卻有兩公里長,約由今新生北路二段四十九巷左近開始,自西北迤向東南直抵今八德路安東街口,這一段波折起伏之路,今日不但在樓房密布、街巷修裁的實際地面無法看出,即使按索於線條或顯分明之地圖,也已不可能。」(《水城台北》)
整整五年,一天五小時起跳,不分晴雨颱風都不曾間斷過的城市行走,我自覺算得台北通一名,而又豈能有一條街道,一條尚餘百餘公尺的街道──以台北的街巷而言,還不算最短的那一類──是我找不到的?
此為我尋找舒蘭街之始。
舒蘭街於民國五十年八月十五日廢街,降格為巷弄。

首先當然是大筆一揮,將地圖上的新生北路二段49巷口與八德路安東街口斜斜連在一塊,算是確定了舒蘭街的大致範圍,範圍內的南京東路三段89巷、松江路184巷與新生北路二段55巷是舒蘭街現存、未被建築物侵噬的路面,這三段彼此不連繫的道路,加以座落新生北路邊的中山區農會舊地址「舒蘭街11巷3號」,如連連看的一個個點,讓我連著連著把整條舒蘭街連出來。
舒蘭街於民國五十年八月十五日廢街,降格為巷弄,廢除降格之因,官方說是名稱不雅,不雅?我忙問母語閩南語的動保人夫,是有何不堪入耳的諧音來著?動保人夫尋思答以,該說「蘭」字結尾的地名多少都有不雅(我偏忘了問其家鄉宜蘭是否亦然),這真是語言隔閡,不然以我來看,以吉林省舒蘭縣命名的這條街,在台北市的道路名稱中實為典雅逸致的一個。
我在二○一三年七月間,頂著彷彿在人脊背上澆下燒熔鋁汁的酷暑日頭,第一遭踏上舒蘭街,走著走著遂明白,與其是名稱不容於人耳,這一歪斜古舊的石子路街道不見容於柏油路嚴整如棋盤的現代城市,恐怕才是舒蘭街真正的消失之因。
舒蘭街是街道也是河,河水自溫州街的九汴頭遙遙而來,第一霧裡薛支線的河神掌理此一和平東路76巷與90巷、瑞安街、復興南路一段、安東街的悠長水路。舒蘭街與第一霧裡薛支線的主流重疊範圍其實有限,約莫自當年的中正路今日的八德路始到南京東路的範圍。那非常窄小的八德路二段267巷,可確定的是第一霧裡薛支線,但是否曾是舒蘭街的南端就不得而知了,畢竟在一九五七年紅通通的「台北市市街圖」(光復後第一張彩色實測圖)上,舒蘭街已不從八德路上起始,而是更北邊的朱崙街,第一霧裡薛支線也略改道,從267巷尾遽然往西,沿龍江路21巷抵龍江路後直角轉北,直到龍江路朱崙街口才回歸原本河道,順著舒蘭街往西北流,至南京東路上止。
舒蘭河邊的童年歲月,只占陳平那漂泊人生中的很小一點而已。
這段路面今日完全消失,化作龍江路左右兩側的建築群落,我曾一度以為走向相同的朱崙街53巷是其殘留,但真正的舒蘭街要偏西數十公尺。遂僅剩舒蘭街橫過大門口的中正國小校友們的兒時記憶,校門口有第一霧裡薛支線殘存水域形成的埤塘,是學童們玩耍與逃躲大人的所在,畢竟在出了事故淹死人後,插上繫著符咒的竹竿封閉了。有初出茅廬任教的年輕教師來到中正國小,就住在舒蘭街上,在他的印象中,這是條國小校門面對的凌亂街道,也許是為紀念,這位年輕教師的女兒也以舒蘭為名。
還有那名住在建國北路上日式房屋的小女生,一樣也是中正國小的學生。媽媽告訴小女生:「外面多少小孩子飯都沒得吃,你們有皮鞋穿,還要嫌東嫌西的吵。」可是小女生仍舊不愛穿鞋,往往脫了鞋襪,光腳踏著煤渣路和雞糞下課回家,趕在進家門前,就著舒蘭河邊洗淨雙腳,拉下裙子抹乾了,穿上鞋襪回家騙過媽媽。
我不免要問舒蘭河神了,曉不曉得那在祂的河水中日日濯足的小女生是何許人也?小女生名叫陳懋平,不過以她這個年紀的小孩子而言,那個「懋」著實難寫了點,故她寫自己的名字,總寫陳平、陳平、陳平的,久而久之,她的名字也成了陳平。這段舒蘭河邊的童年歲月,只占陳平那漂泊人生中的很小一點而已,她用去一生走遍西班牙、德國、美國、西屬撒哈拉、加那利的小島──也是在那裡,她失去那比她年輕許多、在她筆下總顯得很傻很傻的異國戀人,當時兩人相守不過五年,愛情正盛,離習慣了彼此的老夫老妻淡漠階段尚且遙遠,陳平完全承受不了如此打擊,她徒手為他挖墳,若非父母在旁支撐著,她一定就隨他一起去了,這是陳平的大姊在日後的回憶。
陳平回到台灣,最後的那十年,她過得堪稱精彩,卻仍是竭盡一切方法尋覓、聯繫亡夫的歸去之處,哪怕隻字片語也好。然而上窮碧落下黃泉,那人始終杳然,終究她決定親身去至彼方尋找。

根據二戰的美軍轟炸地圖,第一霧裡薛支線已近乎廢棄。
那是陳平的舒蘭河,是第一霧裡薛支線主流與舒蘭街重疊的部分。第一霧裡薛支線主流在南京東路上離開舒蘭街,因為某些緣故,我無法跟隨它到底,在此先大略交代它的去向。通過南京東路後的這條河,由第一銀行旁的南京東路三段109巷東北流,穿越彼此垂直的龍江路、長春路與遼寧街,沿途在龍江路155巷8號、長春路293號、遼寧街209巷25號、長春路327巷8號這幾戶比左鄰右舍都要矮小的房舍留下河跡,在復興北路190巷口以北幾步路處穿出來到復興北路上,此處的第一霧裡薛支線與下埤的西端極其接近,兩者甚至相當像的,是一大一小倒著寫的L字。第一霧裡薛支線短暫繞至復興北路東側,兩者交會點應是在復興北路195號處,在兩側高樓間獨獨矮下去的195號很是突兀,正面看的白牆白頂是雅致的咖啡館,然背後鐵皮搭建的潦草建築仍是露了餡,加以一大片形狀並不方正的停車場,讓人十足相信這是第一霧裡薛支線所剩不多的殘留之一。根據二戰的美軍轟炸地圖,第一霧裡薛支線已近乎廢棄,水量很少,然仍有幾處河道埤塘,眼前就是一處,就在倒寫L字的轉角處,這處埤塘存在的時間很長,光復後的台北市街圖尚能見其蹤跡。
復興北路東側的第一霧裡薛支線,約莫走在興安街139巷、形如六足怪蟲的興安東區國宅後方,在復興北路與民生東路交口的民生大樓旁通過民生東路。大陸工程的民生大樓有台灣諾基亞公司進駐,玻璃帷幕與清水混凝土的大樓,動保人與我見此不免又要笑,看哪是安藤忠雄設計的大樓!這是我倆的老哏,跑日本跑了許多年,近些年眼見美術館之類的公共建築越來越多出自安藤忠雄之手,我倆是有些受不了其風格的,難免要拿他標誌性特色清水混凝土來取笑一番,看哪這個房子是安藤忠雄的看哪那個工地也是安藤忠雄的……到頭來發現安藤忠雄設計了最多的東西就是公廁,還有道路分隔島。
過了民生東路後,第一霧裡薛支線直到復興北路313巷口左右才又回到復興北路西側,不過此處於我而言是盡頭了,我無法再追下去,只能目送它進入龍江路與錦州街切劃成四個象限的那一大片街區,那是動保人與我在這座城市中永遠無法再踏入的禁忌之地。
此大院似的米白色建築名叫如意新村,我很早很早就來過。
故我以舒蘭河代替第一霧裡薛支線的主流去追索,第一霧裡薛支線於進入南京東路三段109巷前一分為三,一條主流與兩條小給水路,其中往西北的小給水路便是舒蘭河,它一路行走直至新生北路上、比它龐大得多但也年輕些的特一號排水溝邊結束。
舒蘭河首先走南京東路三段89巷,儘管舒蘭街於民國五十年廢街,這一小段巷道卻以舒蘭街之名存續到世紀初,也許就是舒國治所說的,那最後的一百多公尺的舒蘭街了。這段舒蘭河,河岸荒涼,的確很難夠格稱得上是街,除卻前段的咖啡館與公寓,放眼便是蔓生著瓜藤的荒地與停車場,由紅磚斷垣區隔著。在這段路結束於建國北路二段11巷前,右邊幾棟日式老房在構樹與血桐斑駁的樹蔭下,老房木材碳黑風化,環繞以二丁掛與鐵皮的加蓋部分,與它們一街之隔的華固雙橡園豪宅區,過去也都是相似的日式房屋區,至少在動保人為她的《古都》踏查時都還是如此。
在舒蘭河流經的89巷口,若稍稍偏離河岸,西行數步,一棵雀榕、幾株尤加利、一蓬亂竹後,是一圍牆環繞的兩層樓米白色建築,呈長條狀的此建築分作兩區,以龍江路120巷為區隔,兩者接鄰著種咖啡樹的復華公園,彼此垂直。此大院似的米白色建築名叫如意新村,我很早很早就來過,彼時我尚且不知舒蘭河,不識河神。
那是深居簡出的外公除幾年一度的海峽兩岸京劇盛會之外,少數會出遠門的時候。極其尋常的外公牽著孫兒的背影,我們一塊來到如意新村,從還算不上玄關的進門處上了二樓,長走廊盡頭的房間,是舒暢舒公公度過下半生的斗室,即便當年我以小學生的視角,也著實訝異於那間斗室之狹小得不可思議,一床一桌一書櫃,便塞得斗室只剩得一條過道。即便是倆瘦弱單薄的老人與一小學生,在那點空間中也狹擠到難以旋身,故我們都出至如意新村外,到舒蘭河邊的咖啡館略坐,多年後舒公公與小苗許是太常光顧那些咖啡館,讓混得熟絡的小苗竟取得咖啡館的大陸加盟經營權。
我看外公與舒公公暢敘,不曉得更多年前、我出生之前、甚至動保人與彼時的我還同齡的舊日裡,外公與舒公公也是這樣的往來,惟場景略不同,多是在我們內湖眷村的家中,而數十年如一日,中間那十九年之久的絕交,也彷彿不存在過。

改建前的如意新村與其周遭都是我想追尋並在腦海裡重建的。
舒公公記述過如意新村,那是政府安置退休士官們之處,住在這裡的老士官們,皆單身無家,連眷村都沒得住。那時的如意新村還未改建,是座紅磚牆內的三排幾十間相毗鄰的隔間。彼時長春路這一帶還荒涼得被稱作市郊小鎮,過去是日本人的重要軍事設施區,二戰期間受美軍密集轟炸,我不免想起那張有些不精準的美軍城市地圖,想著這一片地面在那張灰色圖紙上的模樣。改建前的如意新村與其周遭都是我想追尋並在腦海裡重建的,如村外的水泥路與停車場,如老兵們口中買日用品或請喝酒或上教堂的「鎮上」與菜市場,如可眺望的有著大覺寺的後山,如總有著奇異甚至鬼魅般故事的「號外」——那間大院邊緣,沒有編號的魚鱗板的孤零小屋,屋外是夾竹桃的影影綽綽……我時常想著這些早已找不到的東西究竟錯落在何處,只因今日的如意新村周遭,水泥路已成柏油路,停車場還多著,但多為養地之用,應早已不是當年的位置,小鎮被蔓生的都市吞噬下去、融成一片了,原本隨處可見的夾竹桃因劇毒而幾乎從這座城市中被剷淨,改建後的如意新村逐漸空蕩,這裡的居民是只有離開而無遷入的,老兵們都太清楚了,當隔房的鄰居數日未現身又房門深鎖時,就該是找人來破門的時候,然後便是退輔會的人來,在老兵的身上跨來跨去,頭一個就是搜走抽屜裡的印鑑存摺。
及至外公去世,我與舒公公仍往來不輟,是為戲友。
是的京劇,我始終是個興趣狹隘之人,長久我只聽京劇(其中九成九是老生戲)與搖滾樂(其中九成九是披頭四),曾圖收聽之便將兩者燒錄在同一片CD上而慘遭眾人口誅筆伐:「為什麼聽完了〈坐宮〉之後會是〈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因為是我最喜歡的兩個段子)
舒公公與我的戲友交流,多半是我將從三台或重慶南路秋海棠影視挖寶來的京劇錄影帶借給舒公公轉錄,就在那狹小斗室的臨窗的書桌與貼牆的床鋪之間,那一櫃子的京劇錄影帶,是舒公公多年蒐羅、製作的,我非常榮幸能為充實其內容盡一份力。舒公公的京劇錄影帶製作得深具質感,手撕的兩長條棉紙糊上錄影帶脊背,那兩張手撕紙一大一小相疊,相疊處紙厚棉白,毛筆字寫上戲名與劇團,外圍的單層紙隱透著錄影帶的漆黑,宛若一圈不規則鑲邊,每一圈鑲邊,都是手工業才有的獨一無二。

房中仍是我幼年時見過的,一床一桌一書櫃。
世紀初兩千年左右,舒公公生病住院,因此遇上奇女子小苗。小苗苗青,本名苗維香,在大陸有著精彩極了的人生(如她最常跟我們說起的,她曾做過的中越邊境走私生意,還因此被拘捕進警局)。沈從文說:「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小苗歲數介於動保人與編劇大姊之間,那般人生閱歷卻是兩人的大書,聽得排排坐乖如小學生的兩人瞠目結舌。我仍好奇是什麼樣的困境讓她必須捨棄這樣的人生,來到台灣作一名看護。她是醫院中公認對付難纏病人的好手,也是唯一願意看護臨終者直至其離世的。小苗說,那都是作功德,她說起人臨終的種種跡象,讓動保人嘖嘖稱奇不已的是人之將死,最明顯的是舌頭會縮水變短,此不明原因的徵象,與我大學時在民俗學課堂上學到的殯葬冷知識並無二致。舒公公便是小苗擅長應付的難纏病人,A型處女座的舒公公,彆扭執拗起來連我們都受不了,往往暗罵幾聲:「這個A型鬼!」小苗給派去看護兼應付舒公公,卻是一眼就看出舒公公的不同於常人,並非只是個鄉音重到聽不懂、脾氣古怪的老頭,兩人於人海中的相遇,彷彿孔子與麒麟。
舒公公出院返家,小苗也跟著回到如意新村,那時如意新村人口已稀,小苗得一空房安身不難,仍繼續看護工作,同時跟著舒公公學,學讀書,學棋,學書法。小苗亦照應院中老兵們,老兵們見其人可信,也樂於將自身珍視、於他人眼中無甚大價值的收藏委託她處置,如郵票,如剪報,或是像舒公公那一櫃子的錄影帶,以免到退輔會人員破門進來、在自己身上跨來跨去的那一日,給當垃圾收拾了去。
二○○七年舒公公就在如意新村外跌傷,到一個月後於安養院中去世為止,沒能再回到那如意新村二樓邊角的房間過。編劇同著國家文學館人員至那斗室收拾舒公公來不及整理(甚或滅證)的遺物,細細裝箱封存,將捐贈與國家文學館。房中仍是我幼年時見過的,一床一桌一書櫃,任何人這般蝸居大半輩子,房中總有些私密甚或不堪之物,而舒公公的房間卻不然,這好叫我們感嘆,舒公公真就是個清峻、表裡如一的君子。

從我們這兒熟知小苗生平為人的侯導於是乎感嘆,這世間又少了一名俠女。
那之後的六年,小苗仍是過著琴棋書畫、物質生活降至最低的半隱居日子,彷彿舒公公尚且在世,她仍有著許多闖蕩的機會,如同她在大陸時的前半生。她是在二○一一年得知罹癌的,於是返回大陸過了兩年,在深山中修行,一貓一狗為伴,如此直至她二○一三年辦妥一切後事回到台灣,五月住進醫院做安寧療護,六月離世,過程中沒有麻煩到任何台灣的親友包括我們家。她並簽妥了捐贈遺體供作大體解剖教學的同意書,她說台灣社會惠我良多,理當有所回報。也因此,醫院護理人員對她皆多一份敬重,悉心看護她直到最後一刻。此一切,每天帶著上市的水梨或著新燉的魚湯、花樣天天翻新前去探望的編劇,全都看在眼裡。
那個六月的日子,我在偶爾還會飄雪的內蒙古,當時《刺客聶隱娘》拍攝得正如火如荼,我們陪著聶隱娘與精精兒這兩位俠女在白樺樹林子裡悶頭打了半個月,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一日收工接到台灣來的簡訊,從我們這兒熟知小苗生平為人的侯導於是乎感嘆,這世間又少了一名俠女。
我們是在小苗走後才識得她來台的結婚對象李伯伯的,李伯伯也是退伍老兵,九十多歲的人,硬朗極了的身子惟是耳朵不靈光了。小苗始終照應著李伯伯,並非像一般假結婚的夫婦來台後便不聞問。及至我們一同作為親友,與李伯伯出席陽明醫學大學的結業典禮,典禮上播放的感謝投影片,羅列大體老師們生前種種,生平、與家人的生活照,為讓學生們深切體悟到他們都曾經是活生生的、有親人有名字的有人生的人,而非做過防腐處理失了模樣的大體老師。在投影片中,大體老師們的一生皆充實多彩,唯獨小苗,只有名字與生卒年,一張照片而已。李伯伯對此耿耿於懷,覺得「她這一生顯得太冷清淒涼了」,乃著手蒐羅小苗生前種種,編劇則充當耳朵不行的李伯伯與醫學院的聯絡人,一點一點將小苗本來寥寥兩頁的投影片充實起來。
我想李伯伯對小苗,是見過她極其豐富精彩的一生,不願她留給世人的印象是路倒的無名屍。而我對舒蘭河何嘗不是如此?不願它在他人眼中,只是一條臭水溝。

作者小傳─謝海盟
一九八六年生於台北市,二○○九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穆斯林,跨性別者,喜歡無用的知識,現職電影編劇與自由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