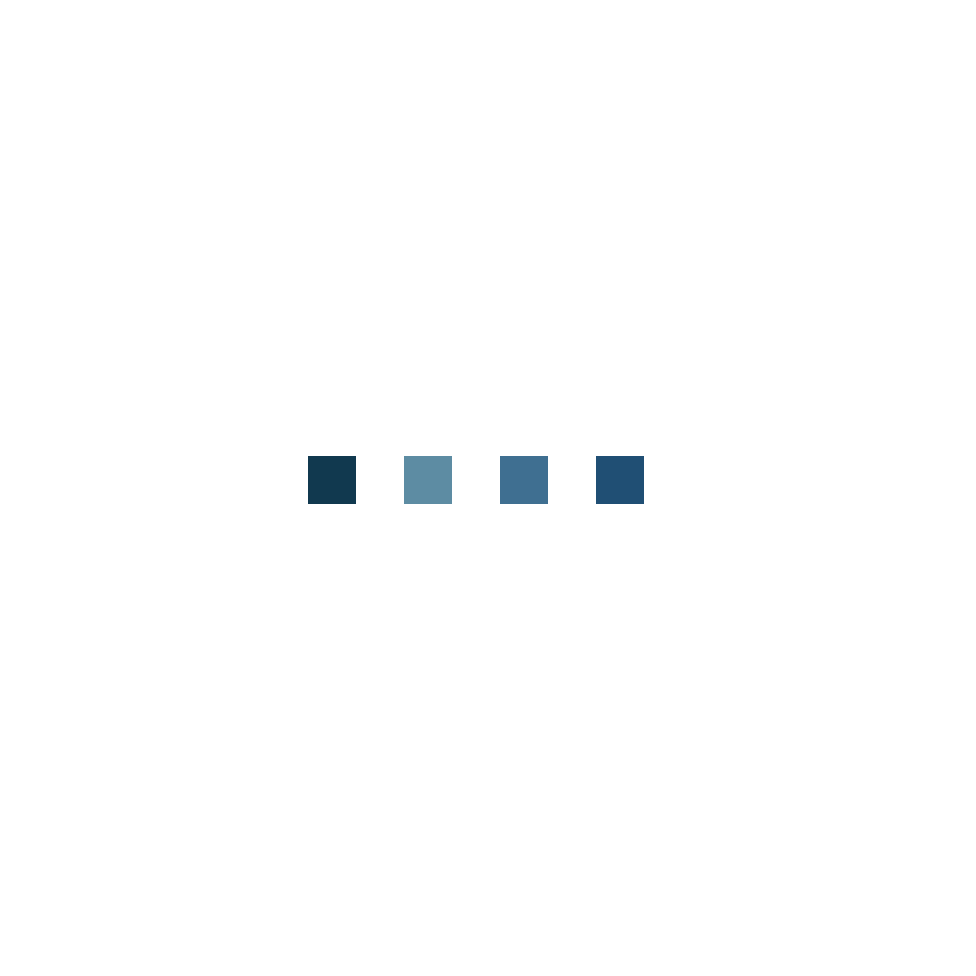王道還科普專欄〈靈魂的神祕蝴蝶〉全文朗讀
我還記得幾篇大一英文課本裡的選文,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塞伯回憶大學生活的名篇。塞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是美國作家、插畫家,在大學不主修科學,可是必須選修一門生物課才能畢業。他選了植物學,顯然失算,因為植物學有實驗單元,其中之一是以顯微鏡觀察花瓣的細胞,而塞伯用顯微鏡看不到任何東西,不是一片漆黑,就是一團乳狀糊。老師用盡一切校準伎倆都無濟於事。有一次,塞伯居然看見了有模有樣的東西,立即動手將它們畫下來,好交作業。老師卻氣急敗壞地告訴他,他看見的是自己的眼睛。原來顯微鏡底座附近有一面小鏡子,將光反射到視野裡,生物組織切片的細節才看得清楚。塞伯到底怎麼搞的,我至今仍想不透。
依賴顯微鏡做研究的學者
不過我對塞伯的敘事細節記憶猶新,並不是因為那個謎團;他教我想起高中生物課本裡提到的德國動物學者魏斯曼(August Weismann, 1834-1914)。魏斯曼在1880年代發表「生殖質」理論,主張生物胚胎中的生殖組織與身體組織已經分化,因此在生物一生,改變身體的力量不會波及生殖組織。換言之,父母遺傳給子女的特質,在父母出生前就注定了,不因他們的後天遭遇而改變。魏斯曼做了一個著名的實驗:從小就切除尾巴的小鼠,生的子女仍有正常尾巴;連續五代,以人工切除尾巴的小鼠,子女一直有正常尾巴。這個實驗結果成為否定拉馬克機制──用進廢退──的重要證據。有趣吧?
但是課本的敘事並不止於鋪陳科學事實,而是繼續告訴我們,魏斯曼本來是依賴顯微鏡做研究的學者,30歲因為視網膜過度敏感,被迫改變研究方向。1886年他妻子過世,眼疾加劇,更依賴學生的觀察,連閱讀都要請人代勞,包括科學論文與消閒作品。他苦思觀察資料的意義,「生殖質」理論才逐漸形成。後來我發現他40歲那年對友人說過這麼一句話:「許多人以『事實不足』為藉口,不去構思理論。可是,沒有理論的話,怎麼知道尋找哪些事實?」眼疾使他專注於理論,才能在數據(data)叢林中找到出路。
亞里斯多德在2300年前已根據月食推論出大地是球體
因此我讀到塞伯的故事,不免期盼他也能絕處逢生,沒想到植物學那門課他因而當掉兩次,拿不到畢業證書。至於塞伯也有眼疾──小時候玩「威廉泰爾」遊戲,被哥哥射中一隻眼睛──是我畢業以後才知道的。
其實我對觀察(或事實、數據)與理論的關係,一開始不甚了了。塞伯讓我想起魏斯曼,只因為情境太相似了。而我們從小的科學教育,一向強調觀察,在日常生活中,「數字會說話」是強有力的套語,政客批判對手、我們參加辯論比賽,都用得上。很少人敢反嗆:數字不說話,說話的是人!只有台電拿出的數字例外,總有人指控台電說謊。
豈止數字不會說話,眾目睽睽的耀眼事實,同樣理未易明。前些日子熱鬧了一陣子的日全食便是好例子。全世界不同的社會對於日月食都有不同的想像,無非怪力亂神,亞里斯多德卻能在2300年前根據月食推論大地是球體。他的證據古代智者都見過:月食食影的邊緣總是圓弧形。他的推理透露他對月食成因的理解與現代科學家無異──大地的影子投射在月面上。亞里斯多德還進一步推論:地球必然很小。因為在地面上的不同地點仰望星空,會看見不同的星象。那是地球很小、地面曲度很大的結果。
學者解剖人腦,關心的都是腦子中間的小空洞 ──腦室
不只天象,我們對自己的想像甚至影響了我們觀察自己的方式。話說西元二世紀,也就是華佗、張仲景的時代,西方的人體解剖學研究出現了重大突破,希臘醫師蓋倫(Galen, 129-199)以動物實驗證明:全身的神經都發源於腦子。可是西方的神經科學並沒有因此突飛猛晉,因為自蓋倫以降,學者解剖人腦,關心的都是腦子中間的小空洞──腦室,認為那是靈魂的居所。靈魂難以捉摸,以解剖刀揭露腦室供人憑弔,聊勝於無。18世紀末,臨床觀察與解剖學結合之後,我們熟悉的大腦「話語」才誕生。

19世紀中,醫師已有堅強的證據,顯示大腦皮層前額葉是人格中樞。1860年代,法國醫師發現大腦左側前額葉的語言區;1870年代,德國醫師發現位於左側耳孔正上方的顳葉有另一個語言區。那兩個語言區要是受傷,產生的失語症症狀迥然不同。整個19世紀,學者以簡陋的工具在大腦皮層上找到了一個又一個功能區,分別控制身體的肌肉與感官。可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關於腦子構造的細節學者仍有重大歧見。
原來腦子是由緻密的細胞構成的,一般的染色法使密密麻麻的細胞全都現形,反而令人看不清細胞與細胞的關係。關於腦子的構造,當時流行兩種理論,一是腦子裡的細胞彼此聯通,不再有個性;另一種主張神經系統與其他系統一樣,以細胞為單位,只是細胞之間的互動機制不同。而學界在18世紀末就發現神經衝動是以電流傳導的,因此「聯通說」是主流。
百年前的觀察、描繪,對新世紀的好奇者還有什麼價值或意義?
最後義大利病理醫師高爾基(Golgi, 1843-1926)意外發明了新的染色法,使神經組織中只有一小部分細胞染上色,終於讓人見識到其中的細緻結構。西班牙醫師卡霍爾(Cajal, 1852-1934)再接再厲,改良了高爾基染色法,使染上色的細胞纖毫畢現。他們一齊獲得1906年諾貝爾生醫獎。有趣的是,高爾基在諾貝爾獎演說中繼續支持「聯通說」,而卡霍爾以同一染色法獲得的證據鼓吹神經元學說──神經元是神經系統的構造、功能單位。(案,神經系統中有兩種細胞,除了神經元,還有神經膠,它們的功能是輔助、支援神經元。)






1930年代,電子顯微鏡問世,證實了神經元學說。可最近幾年,卡霍爾手繪的神經元圖片選輯再度問世,英語世界就有三本新書。那些百年前的觀察、描繪,對新世紀的好奇者還有什麼價值或意義嗎?以卡霍爾的話來說,他的研究
就像昆蟲學者在田野裡追逐彩色斑斕的蝴蝶,大腦皮質裡嬌嫩、窈窕的細胞,是靈魂的神秘蝴蝶;研究那些蝴蝶如何鼓翼,也許有一天能釐清心靈生活的祕密。
百年前第一流的科學家必須利用想像鼓舞他揭露的解剖學事實,以解說靈魂、心靈生活。今日的科學家呢?

作者小傳─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從小喜歡閱讀,但是從未想過寫作,因為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兩次皆遭退稿。大學三年級起意外接到翻譯稿約,以後寫作亦以翻譯為起點(意思是抄襲)。在思想上,對於「思考」產生全新的認識,是在高二暑假讀了《西洋哲學史話》(台北:協志工業出版)、《相對論入門》(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兩本書。從高一起就對演化生物學發生興趣,後來以生物人類學為專業可能並非偶然,可是對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興趣從未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