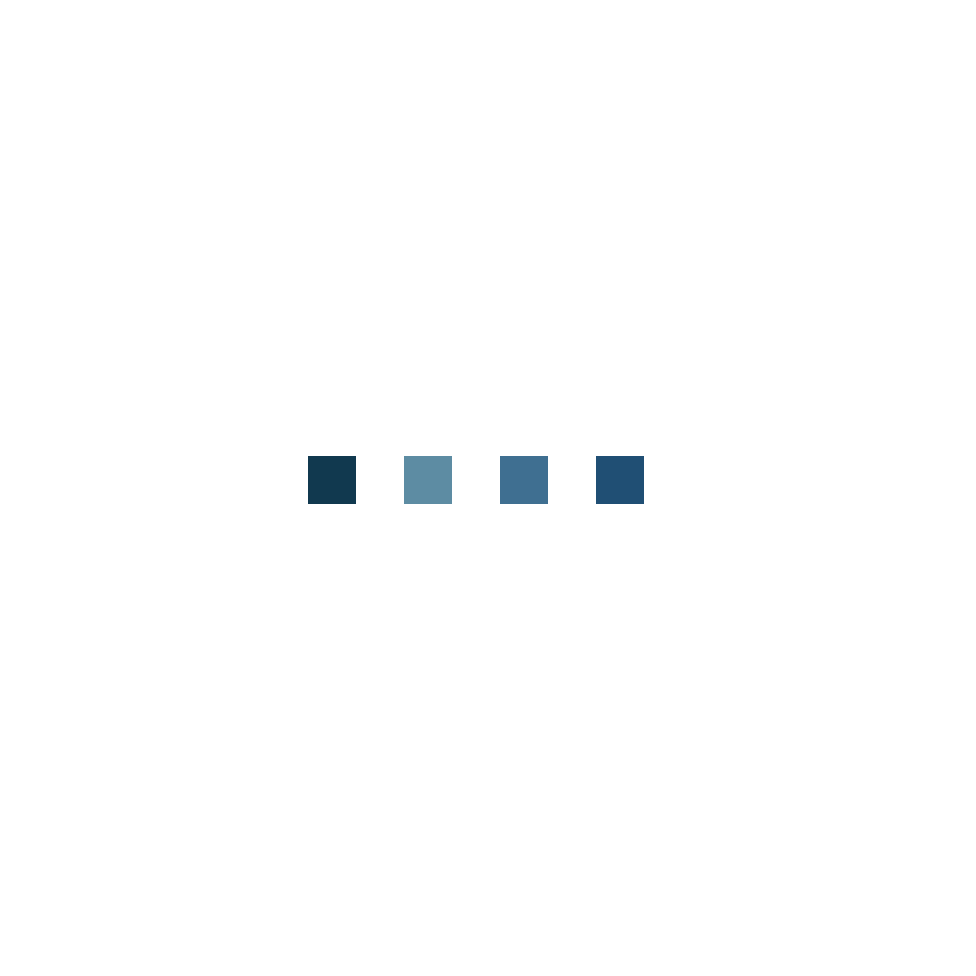68歲的山多瓦現居離古巴只有140多公里的邁阿密。昔日的古巴傳奇,如今入籍為美國公民,對卡斯楚有再尖銳的批判,言論自由的大罩子都會保護著他。今年9月,他受兩廳院邀請來台演出。他的人跟所演奏的音樂一樣奔放,幾乎像不需休息。演出前一晚,他為台灣年輕的爵士樂手上大師班,給建議時不多話,因為每講幾句手就黏到樂器上,從小號、鋼琴到打擊樂器樣樣在行。大師班結束後已是晚上9點半,他抽完雪茄又變一尾活龍,但就連30分鐘專訪也坐不住,手在鋼琴上滑了幾段旋律,才甘願回答問題。

他拿著一支和臉差不多大的iphone,保護殼上印著一大幅美國國旗。這種圖案大概連美國人都只會在國慶日拿出來,他彷彿是要跟眾人宣告他對美國效忠與獨愛;但在兩廳院為他舉行的記者會中,他卻又跟口譯抗議:我講英文不需要像妳一口美國口音!
這種矛盾也顯露他的認同錯亂。山多瓦1949年出生在共產古巴,人民生活貧窮困苦,父親是汽車修理工,他是家族裡第一個對藝術感興趣的孩子,從鄰居那借來各式各樣的樂器自學,最後選定的是最像自己個性的小號,「小號有最顯著的風格,可以吹出輕聲溫柔的音符,也可以製造強烈大聲的音色。」他對音樂的狂熱程度,讓父母一度以為他精神不正常,「但他們根本阻止不了,我一拿到樂器就無法自拔。」山多瓦當兵時偷聽爵士樂而入獄,只因古巴當局認為那是「帝國主義的聲音」。1990年,41歲的他叛逃古巴,到美國開啟人生下半場。
「在古巴的每個事物都好令人垂喪,幾乎看不見天亮的地平線,常常付不出電費和菜錢,時間好像永遠卡在1950年代,建築物都要倒塌的樣子。」每每問及在古巴的回憶,他就像個牧師反覆回答:「昨天已成歷史,明天又是未知,我們只能好好活在當下。」在古巴的日子太貧苦,他訓練自己成為活在當下的人。
他的妻子原本是在古巴外交局工作、讚頌卡斯楚的公務員,他自己則是名氣不小、政府重金栽培的樂隊成員,山多瓦有10年的時間都在想如何逃跑,最終才讓妻子認清古巴專政的現實,願意與他走。1990年,他趁與恩師迪吉.葛拉斯彼(Dizzy Gillespie)在國外巡演時,緊急申請美國庇護。但這個計畫註定無法周延,連對父母親都要保密,還得把時值役齡的大兒子留在古巴。雖然家人之後都順利到美國會合,那段煎熬時光仍是一顆不可刺破的氣球,再不堪的過去他都只用一句,「音樂是少數能治癒你心靈的東西」帶過。
他每講幾句話,就會激動地安插一句「感謝上帝」!拉赫曼尼諾夫( Sergei Rachmaninoff)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在他心中地位有如聖經,總能平撫他的心。拉赫曼尼諾夫崩潰狀態時,曾在醫生的引導下以作曲療癒心靈,最終完成最偉大的鋼琴協奏曲系列,1917年俄國革命後,他也被迫離開祖國,臨終前入籍美國﹔山多瓦最愛的電影則是《刺激1995》,談起這部電影時,他幾乎要從椅子跳起,「我愛極了那部電影、愛極了!」還不用問他原因,他就滔滔不絕開始解析劇情,「電影裡的主角被錯放進監獄,因為我也曾經入獄,彷彿跟著男主角一起見證整個不公義的過程,當他能逃跑時,我也跟他一起邁向自由。」
2013年歐巴馬親自頒給山多瓦自由勳章,距離他「投奔自由」到美國,已過了27年,他卻感覺恍如昨日。他聊起大兒子在早晨的咖啡時光與他討論夢想,這個對一般人再平凡不過片刻,卻讓他嘴角上揚、露出欣慰的神情,他們終於是有資格談夢想的人了。在大家早已不談美國夢的21世紀,山多瓦的爵士美國夢似乎還在發酵。
以下是我們的訪談文字記錄:
鏡傳媒(以下稱「鏡」):你除是傑出小號演奏家,也是錄製過超過60張專輯、為12部電影編曲的作曲者,可是你最出名的仍是那四個八度音的驚人紀錄,對此你有什麼看法?今年68歲的你,如何維持表演水平,每天如何練習?

阿圖羅.山多瓦(以下稱「山」):每次我去演出,大家都只會提到我的四個八度音,觀眾沒聽到我演奏高音還會有點失落,這令我有點困擾。我想在這個世界留下的是我創作的歌曲,因為那才是真正永恆的傳奇,可是大家聽小號時就只想聽它大聲或高音,而我只想把音色演奏得很美,這也是為什麼我每天花最多時間練習的,都是基本音階。
每天早上連牙都還沒刷,我就會先坐在鋼琴前即興,即使只有5或10分鐘,那就是讓我每天想起床的動力。我即興的技巧是跟葛拉斯彼學的,他跟我說,只要坐在鋼琴前面,音符就會浮現到你眼前,因為鋼琴是最好視覺化音符的樂器,可以看見你彈出的每個音。大家喜歡聽我吹高音,好像追求越高音就越厲害,當我到達那個境界之後我也十分欣喜,可是鋼琴讓我能夠完整聽到樂幅跟和弦,教會我用水平的方式欣賞音樂。
鏡:你的父親是汽車修理工,15歲進入古巴國家藝術學院學古典小號之前,都是自學樂器,家族裡有其他人也是音樂家嗎?
山:我不只是整家族裡的第一個音樂家,也是第一個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人,家人的第一反應也是:你要當音樂家嗎?你瘋了嗎?根本養不活自己。但他們也沒得選,因為我非常篤定也下定決心,從來沒有遲疑過。我也不知道這種與生俱來的節奏感是哪來的,我從小就喜歡到街坊鄰居那串門子,借大家的樂器來玩。我腦袋無時無刻都會浮現旋律,所以去電影院時也會有點困擾,因為會不小心隨電影原聲帶哼起歌,其他人就會瞪過來。
感謝上帝因為有音樂,音樂救了我的命,我才沒有變成一個完全鬱悶絕望的人,即便當我還在古巴、在我人生中最糟的時刻,都還能有音樂,音樂永遠都是我靈感的來源。我拿起小號的時候,會覺得這是我人生的任務,也是我被送來地球的原因,所以我常常覺得上帝把我當作一個工具(instrument,與「樂器」諧音),用小號跟觀眾分享我的情感。

鏡:你跟恩師葛拉斯彼的故事廣為人知,可以談談你是在什麼契機接觸到爵士樂?以及如何與他相遇的嗎?
山:1967年有次,有人放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和葛拉斯彼的音樂給我聽,問我有沒有聽過爵士?我聽到時好驚艷,覺得他們開創了我從沒想像過的風格,好自由又好有表現性。那時起我開始偷聽美國之音的爵士廣播節目,當兵時還因此被監禁3個月半,只因政府說爵士是帝國者的音樂。後來我進到古巴政府資助的樂隊,雖然在當地很有名,可是古巴獨裁政權不讓我們演奏爵士,我們需要非常謹慎選擇曲目和在臺上說的話,活在那樣專政的政權中,更不可能有跟大唱片公司簽約、在世界舞台露出的機會。做為一個藝術家,你當然希望能自由傳達想法,但在當時卻完全受政府監控,被強迫做個傀儡,那真的對我心靈造成莫大的沮喪。
相隔十年後的1977 年,有人告訴我葛拉斯彼要來哈瓦納表演,那年我26歲,我開著幾乎要解體的破車衝到碼頭迎接他,根本也沒想到他會接受我的邀請上車。那天是我人生的轉折,遇到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甚至成為我的導師,他後來常常跟我坦承,說他不知道在古巴能有像我這麼優秀的音樂家,那次他回美國後,便將我們引薦給很多音樂產業的人,幾個月後CBS唱片公司的總裁慕名飛到哈瓦納,把我們邀請到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表演。後來葛拉斯彼也用他與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的交情,趁我們在義大利時巡演時,到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幫助我逃離古巴。
鏡:你2013年 的專輯《親愛的迪吉:想念你的每一天》感動了許多人,也獲得3個葛萊美大獎,痛失這個亦師亦友的夥伴,這些年來想念他時你會做些什麼?
葛拉斯彼是1993年1月6日因胰臟癌過世的,可是我們1991、1992年都還有一起去演出。我很遺憾當時我還在歐洲巡迴,無法去參加喪禮。可是我也得誠實告訴你,某方面我很高興自己不用看見他躺在那方正的盒子裡,我沒辦法忍受看見他病重的面容。因為我想要心中關於他的記憶,是他微笑的樣子。我從他身上學到最重要的,就是對音樂的愛與熱情,而要記得他、或是延續他的傳奇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動不斷演奏他的音樂。當年輕一輩的音樂家們問我:那是什麼?我能光榮地告訴他們:這是迪吉.葛拉斯彼對音樂的貢獻。

鏡:你的人生故事精彩,甚至被改編成電影《深情號角手》(2000)。你現在的生活就像是幸福美滿的結局,成功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兩個兒子和你的父母也都搬來美國與你團圓,但當時要叛逃時,令你最放不下的是什麼?這幾年間都沒再回去古巴了嗎?
山:1990年離開古巴之後,我就再也沒回古巴了,而且也不想,絕不!不!我在那裡有太多糟透的回憶。古巴的共產體制是個完全愚蠢、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它只會扼殺人們的靈魂和性格,殺掉他們對生命的熱情,到最後沒有人有動力做事,大家都太頹喪了,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絕望,當你的生命到這境界時,什麼話也不必多說,就是古巴人民感受的絕望。
可是當時計畫要逃跑,真的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因為你得放棄很多已經擁有的東西,最難受的是要丟下我爸媽,想到可能會跟他們永別是最煎熬的。即便如此,我離開的意志還是非常堅決、完完全全,沒有過任何懷疑或後悔,我覺得我絕對做了正確的選擇。不,不是正確的選擇,而是做出了我唯一的選擇:從那裡逃跑、開啟新生活,有新機會,開始對所有事物都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自由地表達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