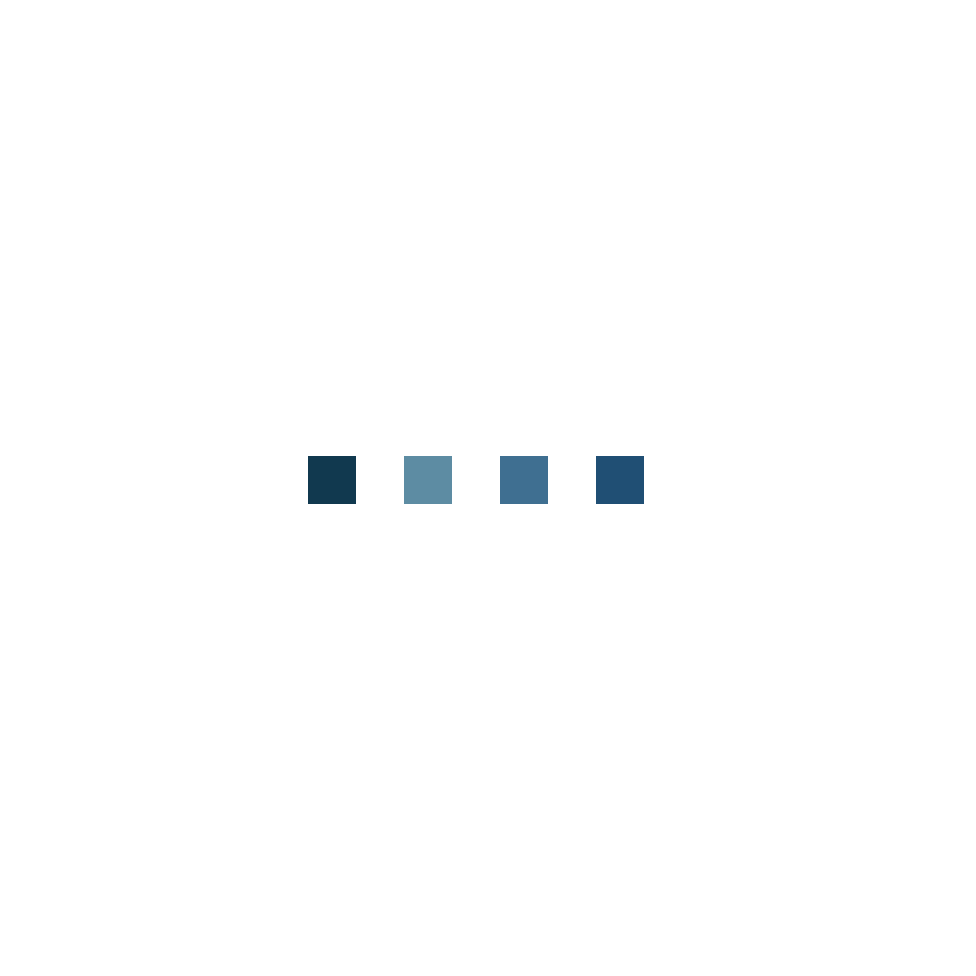黃宗潔書評〈我們有可能理解另一種語言嗎?──《拾貝人》〉全文朗讀
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在其隨筆《羅馬四季》中,曾以一段生動的文字描述自己嘗試以義大利文購物的困窘。經過一連串比手畫腳之後,總算帶著加了蘑菇的蕃茄罐頭離開,直到快到家,他才意識到「自己先前大聲叫嚷,吵著要買一罐葡萄柚醬,而且是加了九層塔的葡萄柚醬。」(p.75)

要買蕃茄卻講成葡萄柚;在餐廳想嘗試地方美食,卻因為隨手亂指得到意料之外的餐點,或許是很多人在旅行或旅居異地時,必然發生的溝通誤差。雞同鴨講的茫然、無傷大雅的誤會,有時甚至會成為點綴旅遊記憶的小樂趣。但另一方面,這些日常經驗卻也反覆提醒我們,當對話雙方操持著不同語言,溝通的困難與「誤譯」的某種必然。杜爾的短篇小說《拾貝人》,就可說是一則則不同語言之間,試圖理解或充滿矛盾的碰撞過程。只不過在碰撞之間點燃的,有時是照亮黑暗的火光,有時則是足以帶來毀滅的燎原星火。
不過,此處所指的「語言」,並非限於不同地域、國家、種族使用的不同語言文字系統,而是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八篇題材迥異的故事,幾乎無一不涉及人與人之間價值系統的碰撞,以及對話的困難。例如同名單篇〈拾貝人〉中,眼盲的拾貝人試圖說服盲目的信眾,不該僅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就相信劇毒的芋螺可以治病,他懇求記者「報導芋螺的危險性,但他們對奇蹟比較感興趣」(p.25);離家多年的兒子因此返家,卻同樣是為了芋螺的「療效」而來,眼盲的父親提醒他吐司烤焦了,只換來一句斥責:「人們性命垂危地躺在你家門口的臺階上,而你只管吐司!」(p.30)父子間的隔閡,遂如同那逐漸烤焦的吐司般,終究難以逆轉。
沒有人有辦法在俄亥俄州複製牛羚與斑馬的遷徙
同樣被隔絕在彼此世界之外的,還有〈獵人之妻〉當中的夫妻。獵人之妻擁有神奇的感應能力,能在觸碰離世動物時看見牠們臨終前的畫面、牠們眼中的天堂;她能看見獵人的夢境,感受到靈魂的飄盪。但是獵人拒絕相信,即使在親友們紛紛發現透過碰觸她,他們也能看見離世親人眼中的影像;即使獵人之妻準確地說出了他的夢境;即使她反覆告訴他:你只需要握握我的手,你就能理解。但他不能。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不同,那是截然不同的語言。
〈Mkondo〉中美國博物學家沃德與坦尚尼亞女子娜依瑪的婚姻,亦是兩種世界、兩種語言的對比。娜依瑪熱衷於她自創的「跨出多一步」的遊戲,但這次她跨越的步伐超越了某個臨界點,俄亥俄的一切令她感覺受困,她開始試著在家中複製荒野:設立蜂房、架餵鳥器、餵食松鼠、甚至和雞農買下一對紅尾鵟鷹。然而荒野無法複製,沒有人有辦法在俄亥俄州複製牛羚與斑馬的遷徙,沒有任何博物館做得到。
除此之外,〈長久以來,這是個葛莉賽達的故事〉當中的兩姐妹葛莉賽達與蘿絲瑪莉,亦可窺見在冒險與平凡、欲望與壓抑、失序與秩序之間的種種鮮明對比。野性之愛與甘於平淡、知性理性的追求與心靈之眼的凝視,在各篇小說中透過不同角色的命運與選擇,不斷交錯著,宛如循環往復的旋律,令讀者低迴思考。
人們以名稱指認萬物,期待將世間秩序盡收其中
而在所有語言之中,最繁複難解的,當屬自然的語言,生命的語言。但在杜爾筆下,這些語言其實並不等待人們去解讀它。乍看之下,這似乎顯得有些矛盾,畢竟其中許多篇章都帶有博物學的元素,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拾貝人〉與〈Mkondo〉:「拾貝人」是退休的貝類學者,僅用手指就可判定手中的螺貝「究竟屬於榧螺科、枇杷螺科,或是筍螺科」(p.13);〈Mkondo〉則透過娜依瑪之眼,看見博物館中「眾人執迷於幫物品命名分類,好像頭一隻破繭而出的橘翼蝴蝶非得叫做『紅襟粉蝶』,好像一個乾巴巴、用大頭釘釘在美術紙板上,標注著『晚蕨』的標本即可道盡蕨草的本質」(p.241)。

人們以名稱指認萬物,期待將世間秩序盡收其中,一如段義孚在《逃避主義》書中所舉的例子,一個納瓦霍族(Navajo)的父親在對孩子解釋細繩遊戲時說:「我們必須把生活與星星以及太陽聯繫起來,和動物以及所有的自然聯繫起來,否則我們就會變得瘋狂或是不舒服。」(p.152)將萬事萬物予以編碼、分門別類,確實足以讓人們感到安心。但我們需要指認、需要專業的術語和知識才能從中感受到意義與愛嗎?深閨芋螺、殺手芋螺這些詞彙,和弱智男孩們自創的「藍美人!姆巴巴雞螺!」(p.31)真的有那麼大的分別嗎?不過,小說並非論述,因此杜爾並非意在提供答案或大道理,而是透過不同角色的不同選擇,呈現這些選擇交織出的世界圖景。
毫無疑問地,秩序和儀式能帶來安定感或成就感,就像〈守望者〉當中經歷過賴比瑞亞內戰種種慘不忍睹惡夢景象的主角喬瑟夫,透過掩埋擱淺抹香鯨的心臟,以及悄悄地在那塊小小的空地上播種,似乎也掩埋了一部分的苦痛與創傷,並因此得以「為自己的生活重新編製出一套秩序、一套規律」(p.186)。〈七月四日大贏家〉當中的美國佬與英國佬,行遍各大洲只為競爭「誰先釣到體積最大的淡水魚」,則清楚呈現出秩序的另一面,其實就是掌控自然的欲望。
我們仍有可能找到進入他人語言世界的入口
但另一方面,當我們試圖將一切事物納入控制之中,失控的欲望亦將帶來不可測的風險或代價:芋螺的毒素無法掌控、療效不可預期,一旦誤觸生死將僅懸一線之間;當伐木工人將每一片容易到達的森林都加以砍伐,狼群最後就只能存在獵人的夢裡。若無視於此,人們為了渴求秩序所作的一切,終究只會帶來失序的結局。

至此,我們或許才能了解杜爾為何在故事中安插了那麼多被排除在主流秩序之外的,失序甚至失語的存在:盲眼的貝類學者、弱智的男孩、擁有特殊感應力的獵人之妻、吞吃金屬的人、偷渡者的女兒、戰爭難民、莊園主的啞女……他們某程度上都是無法被理解之人,無法與身邊的人溝通之人。但如果願意,我們仍有可能找到進入他人語言世界的入口,杜爾並未否認透過知識的界域所能帶來的滿足與意義,但認識世界的語言從來不只一種,它可以是弱智孩子自創的詞語、沉默但有如流水般靈動的手語、也可以是觸碰獵人之妻後,感受到的「赤楊枝葉的味道」與世間萬物「琥珀色的光影」(p.79)。
而當我們試圖跨越語言視域的界線,或許就能進一步窺見這八篇故事的核心語言,那就是生命的自行其是。人類以其意志、知識和欲望改變了世界,在短短幾十年間,就連被視為荒野自然代表的非洲,也不再是過往的非洲了:「山坡地多了數以百計的梯田;電視天線矗立在山脊線上,閃閃爍爍」,但百年一瞬,「對於那些世世代代奔騰於原野中,教導年輕崽仔如何求生的野生動物而言,一百年多麼短暫。」(p.263)牠們仍然以牠們所知與僅知的方式努力活著,有各自的語言與天堂。自然從不浪漫,牠們在擱淺時無從拯救自身,受困寒冰或被水捲走時只能掙扎浮沉,但無論人們如何採集、狩獵、垂釣、定義與改變自然,萬物自有其節奏,並非人力盡能掌握。就算渺小如一隻海螺,也擁有只有牠自身才知道的,攀爬的方向。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