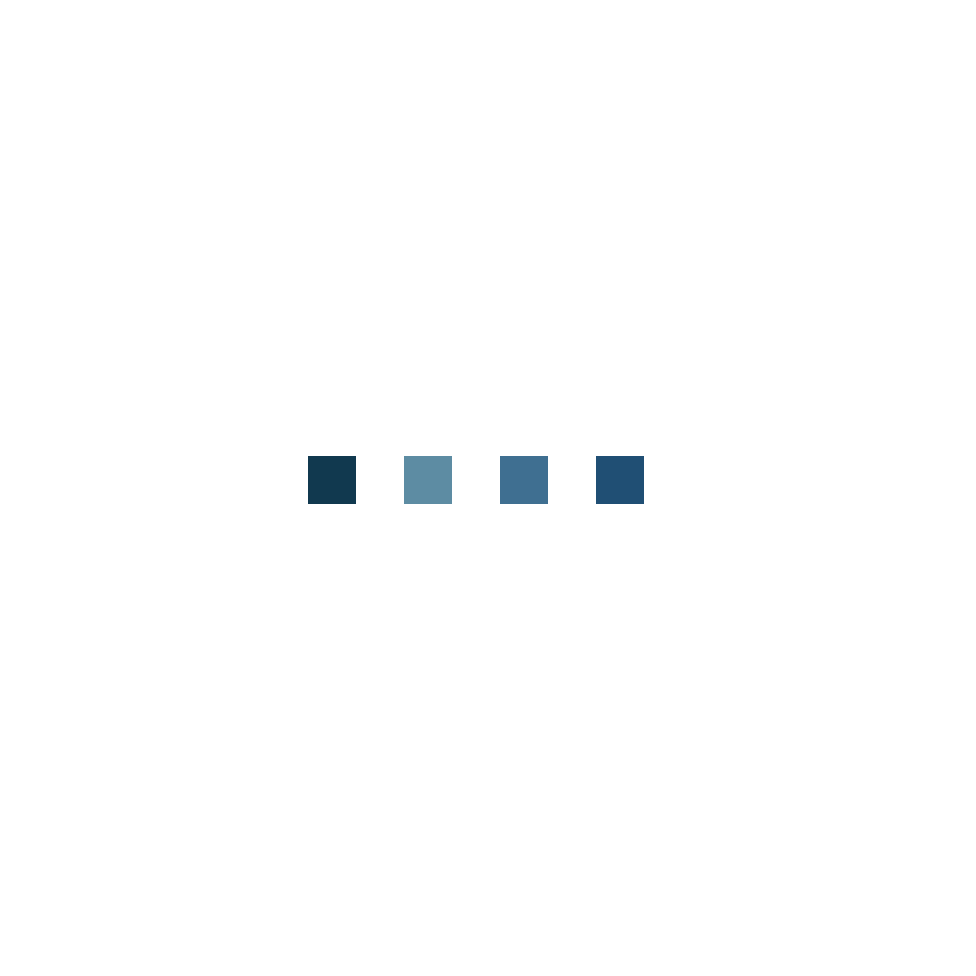盧郁佳書評〈我無法相信自己──《瀨戶與內海》〉全文朗讀
對話總是嶙峋多孔節的,無言坦露出人心經年累月被風浪打的傷痕。有很多話,聽到的當下不察,過後想起,才懂它透露了對方的心事。有很多話一聽就事有蹊蹺,但卻不可碰觸,深究下去彼此就會緊張、有壓力。《生命的尋路人》描述部落青年在海上操獨木舟航行,為了熟悉每一股洋流的起伏,會把頭髮或生殖器用線連在船身上,在他和海的對話中,不放過每一絲細微震盪。日本漫畫家此元和津也的漫畫《瀨戶與內海》就是這樣動見觀瞻,精密掃描海面每一道浪底下,洋流迴力的指紋。對話者操舟,對方是海,對話就是獨木舟。在對話中,對方的心一動,自己也跟著動。有人隨波逐流不知所終,有人奮槳逆流而被吞沒,《瀨戶與內海》卻以耐心操舟,回應每個波動,神技讓人嘆為觀止。以下劇透。
《瀨戶與內海》描述大阪兩個高二男生,每天放學後,坐在學校附近的河濱公園台階上,瞎聊一個半小時。槍打出頭鳥,熱血笨蛋瀨戶因為沒有禮讓服從前輩,而被學長踢出足球社,所以放學不用苦練了,忽然空出大把時間。資優生內海,冷漠高傲不屑與人為伍,放學跟補習之間的空檔,就躲在河邊獨處打發。剛好被瀨戶逮住,天天找他喇賽煩死人,他專門冷冷刺瀨戶一句,讓讀者噗哧笑出來。
河邊就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神聖結界,像是漫畫《荒川爆笑團》、《大川端偵探社》,河邊充滿畸人異事。城市因河流而興,後來雖然寸土寸金,但為防洪水氾濫,必須保留河濱的行水區空地緩衝;人在緊鑼密鼓的勞動時間表之外,也必須守住無目的、不生產,嬉戲、交流、獨處的時間。兩者看似奢侈,對城市和生產卻不可或缺,少了它就會失衡崩潰。
把主觀抒情的漫畫語言刪減到極限
被團體放逐落單的兩個人,沒有目的,坐著練逍話。不事生產的浪費,就像古人犧牲牛羊獻祭給神明,才配得上這空間、時間的畸零冗餘。他們無厘頭玩諧音、雙關語的遊戲,是體制掠奴的陷阱,例如瀨戶一承認考不上大學就會羞愧,例如爺爺教瀨戶與內海「不管人生是不是馬拉松,都得一直跑下去」,語言都在逼人投身升學就業競爭。遊戲,不但逃離了日常語言的監獄,最後還可以像法國大革命的暴民那樣攻打巴士底獄。

就此展開漫畫史上石破天驚的美術設定,八集漫畫像舞台劇固定在一個主景,固定在河邊。其他學校等場景盡量只在對白中提及,能不畫出來就不畫出來,會出現但能少絕不多。河邊以精細的照相寫實景觀呈現,像電玩三百六十度的虛擬網點像素環境。照片轉檔般的背景,在書中是壓倒性的存在。
本書把主觀抒情的漫畫語言刪減到極限,轉而模擬架攝影機拍攝,一切轉譯為客觀理性的光學語言,由熱轉冷。一般漫畫把表情扭曲誇大變形來逗笑,用Q版三頭身、孟克《吶喊》造型表達悲喜。《瀨戶與內海》從不變形。一般漫畫常從現實切換到角色的心象意識幻境,但它在《瀨戶與內海》中的百分比降到小數點以下,多數時候,心象用對白呈現,用手機裡的照片來呈現。要表達中年生物老師跟大猩猩長得有多像,一般漫畫會在生物老師身邊畫個不存在的大猩猩,本書會讓內海在速寫本上塗鴉畫出大猩猩。心象無可避免必須登場時,作者鑿通精神與現實、陰陽兩界之間的通道,把譬喻拖進實物。《瀨戶與內海》的主題和形式恰成對比,用不苟言笑的光學成像,來講白爛耍廢。就像是強迫症,能用的東西一概不用,把自由削減到最低。憋到完結篇,轟然一擊解禁,把先前的自制全部打破。
據說作者作風低調、從不曝光
由此回顧全書,兩人耍嘴皮的話題此起彼落,像是無數荷葉漂在湖面,千百個碎片零落紛散。然後點滴揭露每一片在幽黑不可見的水底全部相連,對話全都通往同一個核心。偶然之下的必然性圖窮匕見,劇力萬鈞。先是鏡頭瞬間突破河景的限制,入侵異世界──內海的情緒深淵。接著,先前避免的抽象表現、主觀心象、抒情視角,全部解禁。像接連擲出手榴彈般,在畫面上大爆炸。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自制和隱瞞在全程蓄積張力,是為了最終內海的自我揭露。令讀者驚覺,正是結尾這個空間,這個不可說的核心,在決定河邊發生的日常一切。
揭露謎底的過程驚心動魄,張力十足。瀨戶很想了解內海,但遇到內海阻抗就立刻裝沒事打哈哈,要靠別人來通靈。好萊塢電影中,警方抵達命案現場,已經被兇手刷洗滅跡,要等鑑識小組噴上顯影劑,在黑暗中才見到滿牆螢光,都是血跡反應。書中追求瀨戶的心機女初美,就是顯影劑,故事透過初美把線索連起來。初美聽說內海從小學一年級至今、臥房家具位置沒變過,就意識到內海可能有強迫症。內海的姐姐相信,強迫症是內海天生如此。這一筆反諷姐姐視而不見,讓讀者知道內海被嚴厲管教,相信自己只要動一動就會受懲罰,不敢越雷池一步。
初美為此上網搜尋,書中只畫她打出字首「AS」,暗示讀者,內海有亞斯伯格症。作者話就說到這了,為什麼不說完病名呢?因為要讀者去想,這是作者遞出一張名片。話說現實中,有許多自閉奇才,都擅長城市全景畫,畫風寫實精密,只要搭直升機巡迴城市上空一圈,就能光憑記憶畫出巨幅長卷全圖。內海同樣擁有照相記憶,過目不忘。手機型號亂碼,他看一眼就能背下來;不需要藍本,憑空就畫出素描、圖鑑畫細節詳盡。使讀者恍然大悟,《瀨戶與內海》照相寫實畫風說明了全書是內海的視角,談論好友怎樣從不可能獲救的精神困境中拯救了他。據說作者作風低調、從不曝光。有可能他也是亞斯,見陌生人對他很辛苦。
內海被接納,衝突被消解
問題應該這麼問,為什麼內海受虐需要照片、日記存證?因為受虐者知道事情太荒謬,講出來別人不會相信。為什麼受虐不講出來求助?因為知道別人不會相信。因為知道別人不會相信,所以受虐者已經不相信自己的話。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都沒有資格存在,沒有資格表達出來。受虐者跟別人之間不存在默契。
乍看瀨戶與內海兩人是相聲中的逗哽和捧哽,瀨戶耍笨,內海吐槽。但讀者很快會明白,其實說笑並非表面上那樣和平,資優生內海以海量知識和詞彙庫,一面倒輾壓足球笨蛋瀨戶,對話張力來自在玩笑中宣洩的攻擊,既是嬉鬧、炫耀腕力,也是競爭、無情征服。
內海總是不自覺、沒來由地處處挑剔,吐槽。輕則好笑,重則翻臉。所以一天瀨戶提議玩「一開口就否定對方的話」的遊戲,把內海的習慣模式,改編成外在規則,要內海遵守。這些社交的顛簸,由瀨戶的觀察所捕獲,透過遊戲設計,讓內海也察覺,有機會觀察自己的暗潮流向,拿捏輕重。在兩人正反申論、即興變奏下,內海被接納,衝突被消解,或激化爆發再學習迂迴和好。過程,都是內海由孤立而學習成為一個人的關鍵。
開頭瀨戶抱怨被學長霸凌,內海傾向壓抑憤怒。然而窖藏的憤怒腐蝕了內海,熟人都覺得內海高高在上睥睨眾人。只有在河邊喇賽時,內海的憤怒既不圍堵、也不洩洪,而通過像蓮蓬頭的無數小孔灑出細細水花,變成無害的打鬧。
暴力來自生存本身,難以妥協
有一回,兩人聽一個形銷骨立的窮漢說,他餓了三天沒吃飯,隨手拿別人皮夾,被揍,就拿刀捅了人。瀨戶聞言上前奪刀追凶,卻被警方當成持刀凶嫌逮捕。這還不是作者要說的,真正的神展開,在接著內海作證說,相信瀨戶就是刺殺路人的凶嫌,因為案發時瀨戶沒有不在場證明,無法排除涉案可能。這是內海開玩笑惡整瀨戶,還是一板一眼的內海真心這麼想?故事開放給每個讀者作出不同解讀。我以為內海真心恐懼,他知道無論是多親近的人,隨時轉過身就會變臉換成另一個人。親近的人突然變得猙獰恐怖,對他也是理所當然。
日本自傳小說《不管媽媽多麼討厭我》作者歌川泰司回憶小學時住在孤兒院,一個院童不斷霸凌他,乍看非常可惡。但那個院童洗澡時,衣服一脫全身都是傷痕。院童怎樣欺負歌川泰司,內海就怎樣輾壓瀨戶,實是壓抑的憤怒在借題發揮。人生長在暴力環境中,往往學會虛張聲勢自保,不懂得怎樣和平相處、協調差異。所以美國貧民窟黑人社群發明了很多儀式來取代幫派暴力,像街頭籃球鬥牛、街舞小子遇見了先互相軋舞、嘻哈擺高姿態互嗆。瀨戶設計這些對話遊戲,就是把暴力轉換為非暴力的裝置。
暴力來自生存本身,難以妥協,過程中內海不斷抵抗瀨戶。結尾揭曉後,回看全書許多小插曲,竟已藏閃點出內海心境。
氣球小丑每次見瀨戶就有說有笑,一轉頭就釘內海。對兩人的明顯差別待遇,原來是在寫內海父母疼愛女兒、虐待兒子的差別待遇。
內海的母親,在全書中都沒有露面
而另一次,內海在不懂規則的情況下,被小丑和瀨戶逼著打手機電玩。內海只見手中電玩主角忽然倒斃,瀨戶和小丑嘲笑內海竟然不知道主角要吃東西,竟然不知道「不吃東西會死掉」。乍看是搞笑,回頭對照內海父親吩咐母親不給內海準備三餐,只給零用錢解決,用精神上的斷糧處罰內海不聽話,揭露電玩主角就是內海的化身。
電玩劇情是牆頭接連掉下「可吃的東西」和「會殺死主角的東西」給主角,玩家必須作出不同反應:可吃的,主角該去吃;會爆炸的,主角該躲開。但內海沒玩過,完全看不出掉下的東西是哪一種,每次都弄錯、害主角死掉,被瀨戶和小丑狠狠嘲笑一番。內海表現的,是在現實中,受虐兒的認知障礙,因為所受的壓迫都以愛為名,甚至小孩子不依靠壓迫者就無法生存,導致受虐者到成年後都還繼續混淆被愛和受虐待,若被愛就會恐懼不安,只有受虐時才覺得被愛。所以內海無法分辨頭頂掉下來的是食物或炸彈,也不懂為什麼大家都能分辨。
電玩這一關的結尾,劇情竟然是電玩主角的母親從牆頭露面,流淚向主角懺悔不斷扔東西下來。這讓讀者發現,虐待內海的關鍵人物之一,內海的母親,在全書中都沒有露面。就算母親是服從、執行內海父親的命令,但母親怎能下得了手呢?母親討厭內海嗎,不愛內海嗎?究竟母親是怎麼想的?當中巨大的衝突與疑問,書裡沒有提。透過電玩的母親角色現身,是作者唯一能談論她的方式。
水太深,不能碰。
有一回,瀨戶隨口形容頭痛,「像被一隻巨手妖怪掐緊腦袋」。這信手拈來的譬喻,在內海追問下,瀨戶開展情節,共同創作出一個RPG電玩式的冒險故事。讀者從結尾回頭看,會驚覺大手怪欲蓋彌彰,一旦妖怪愛上了公主,知道了愛為何物,這時面臨的抉擇是妖怪要變成人類,還是從人類變回妖怪。要說的就是內海的兩難,掙扎要不要用暴力終結受虐。
遇難者通常表裡不一,雖然內心需要支持
其次是瀨戶收集的扭蛋公仔「三毛貝」,來自書中虛構的連載四格漫畫:主角少年的好友是一隻三毛貓,三毛貓就是白底黑黃斑的三色貓,俗稱三花。這隻貓住在雙殼貝裡。雖然一有動靜牠就縮回貝殼裡,只有雙眼窺望追逐逗貓棒。四格漫畫連載在變調的恐怖中宣告爛尾,瀨戶也忽然擔憂起河邊邂逅的三毛野貓會死。三毛貝象徵內海。三毛貝、三毛貓的危機,也是內海的掙扎。
資本主義勞動與競爭,肢解了團體中情感交流的紐帶。壓力在液化崩解人際關係,使精神上遇難的人孤立無援。漫畫《Orange》敘述女主角穿越時空寫信給青春期的自己,要她阻止男同學自殺,《到處不存在的我》的男主角則回到過去阻止行兇。這些漫畫的救亡悲願,就是迫切的改革意識:如果我能以成年後的資源高度來看問題,年少的我會怎麼做?
過去我們往往失之天真樂觀,以為遇難容易認出,以為救難一夕速成。《瀨戶與內海》藉同學田中真二表面沉穩自信、內心自卑憂憤的落差,隔山打牛,影射內海的內外落差,道出了外人辨認之難:遇難者通常表裡不一,雖然內心需要支持,外表卻故作冷漠,因為羞愧而極力掩飾困擾。救援之難,難在即使朋友接近他,無論說什麼,都會意外激起他的緊張痛苦。創傷使他把別人說的話重組為言語暴力來理解,因此一心只想逃離別人,逃不掉的時候他也會對人言語暴力。他的困擾就像是房間裡的大象,彼此既不能提,但無論繞開大象說什麼,他都會覺得在講那頭大象,而無法忍受。自我被暴力所摧毀的人,雖然被說成玻璃心,其實還不待說、早已碎一地,別人的話只是再次把他壓倒在滿地玻璃渣上遍體鱗傷而已。
一次次來回對話,起死人而肉白骨
瀨戶為什麼讓對話停留在表面的文字遊戲?因為無言的體貼。田中真二解釋,體貼感不是表面工夫,而是為別人著想。房間裡的大象不可碰觸,瀨戶偏安江左,打定主意不冒險。既然瀨戶必須對內海說點什麼,又什麼都不能說,那麼就言不及義刷存在感。生而為人,存在感原本就不可或缺。所謂「刷存在感」,這句貶抑的結論,就是語言的暴力,充當生產體制打手,貶低團體中乏人關注的邊緣人、和他們那欠缺情報價值或娛樂效果不彰的語言。其實存在感就像刷牙,當然要天天刷,要是沒刷到就要刷好刷滿。內海的自我原本已稀薄透明而消失,殘骸已破碎一地拼不回來。但透過接龍、譬喻等遊戲的一來一往,內海說一句,瀨戶在拍子上回一句,這回應就向內海證明了內海的存在。一次次來回對話,起死人而肉白骨,內海從虛空中逐漸一點一滴被生回人間。
舊的內海,不知道貓有什麼好,抱三毛野貓的親密感令他陌生不安,感到威脅。就像他不喜歡別人接近,說別人「像環法自行車賽的觀眾(靠選手太近)一樣」離他太近了。
而這個在對話中新生出來的人,卻是在被人喜歡、撒嬌、吵架輸贏中,認識了自己的存在。在被野貓磨蹭依戀、輪流餵貓中,成為需要別人、也被需要的人。
那是嶄新而安全的自己。
本文作者─盧郁佳
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人、《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輯、《明日報》主編、《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全職寫作。曾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有《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