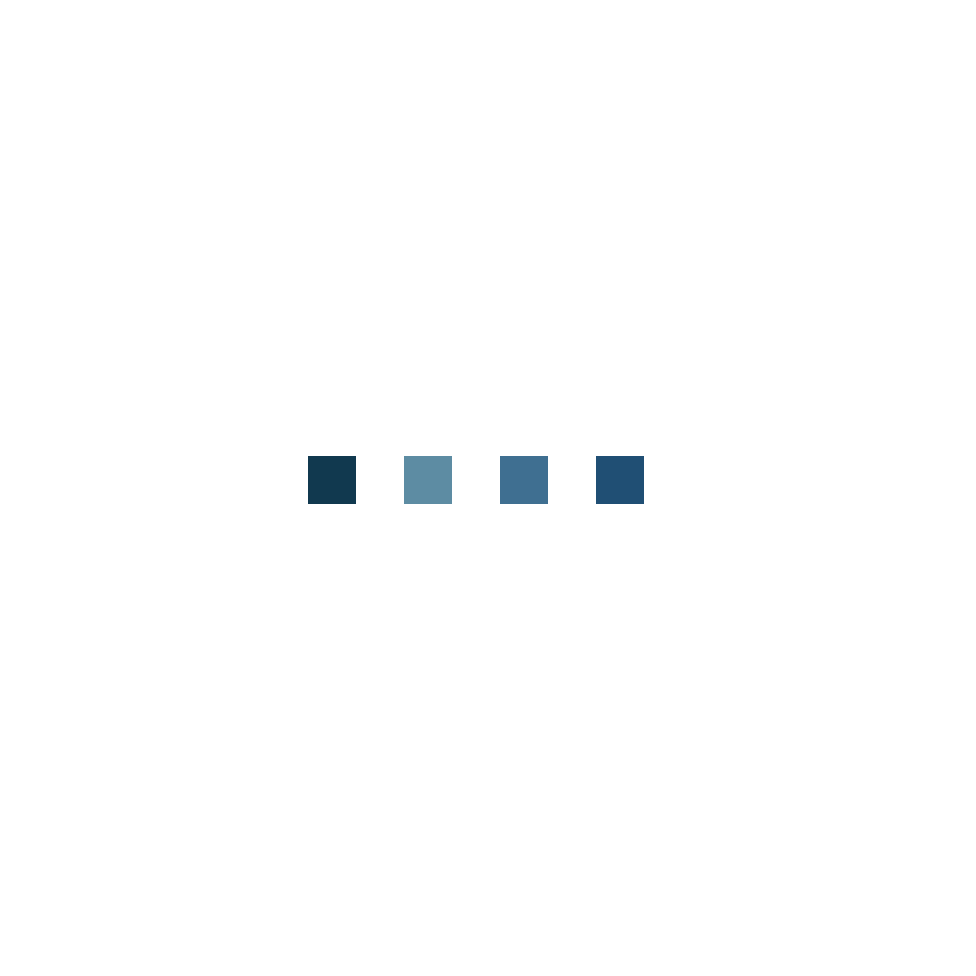廖偉棠書評〈迷宮入口處的回望──《最後來的是烏鴉》〉全文朗讀

這種沉重我們在《最後來的是烏鴉》裡不難窺見,然而更多的是卡爾維諾在沉重之際不忘眷顧他寫及的城鄉無產者所展示的活力與想像力,正是這種細察與想像,讓卡爾維諾有別於大多數1950年代的左翼小說家,使他成為日後的卡爾維諾。因為他在廢墟之上發現了一個迷宮,這個迷宮由人心、命運、文字的曲折組成,《最後來的是烏鴉》就是他走進這個迷宮之前的一次躊躇滿志的回望。
戰後一代人各階層之間的不知所措
回望本身就築構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卡爾維諾。《最後來的是烏鴉》雖然是短篇小說集,但其主題的變化、呼應以及匯總,隱約搭建著卡爾維諾關注的另一個義大利──那個貧困襤褸、階級懸殊、背水一戰的義大利。不看這些,你一定以為義大利只是一個空中樓閣一般的美好世界,就像很多誤讀卡爾維諾中晚期寓言小說的所謂「純文學」愛好者所以為。
如果要尋找意象的對照,今年的義大利電影神作《幸福的拉札洛》可堪成為小說的插圖。但雖然相隔有半個世紀,卡爾維諾的山區農民們在戰火中反而找到了解放自己的機會,不用像《幸福的拉札洛》裡的村民一樣等待聖人的救贖。
最接近《幸福的拉札洛》的,如〈與牧羊人共進午餐〉和〈地主的眼睛〉,就把戰後一代人各階層之間的不知所措,寫得淋漓盡致富有詩意,後者更讓人想到電影裡年輕侯爵與拉札洛他們的隔絕;最後一篇〈誰往海裡丟地雷?〉則像是對前者遙遠的呼應,沒有獲得與權貴們共進午餐機會的漁民,自己製造了一場豐盛的晚宴,不管地雷在海上炸開會驚醒幾個權貴的噩夢。
這是卡爾維諾書寫另一個義大利時樂觀幽默的一面,相類似的還有前面幾篇寫兒童們漠視階級世界的規則的放肆,讓人想起法國諾獎作家勒克萊喬(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早年的「夢多」系列少年小說(Mondo et autres histoires),尤其是〈魔法花園〉與〈爬滿螃蟹的貨輪〉,把底層兒童的充沛精力如夢似幻地展開──正如龐德的詩所預言,這些「野蠻」的孩子,他們「將接管這個世界」。
左翼的悸動,一直是義大利的潛流
但貧窮的刻骨蝕心毋需掩飾,這是卡爾維諾最後的現實主義,如短刀相決,俐落驚心。日後「很卡爾維諾」的超現實段落成為了現實的強烈反襯。比如〈代代相傳〉,文字流動的精彩妙不可言,但越精彩我們就越為貧窮的人、絕望的牛而難過,他們的恍惚出神只能在卡爾維諾的文采中一閃,便戛然而止,回到最鐵板一塊的現實中。〈光禿禿枝椏上的晨光〉與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貧窮版本的《樹上的男爵》,有著同樣渴望逃逸與隱藏在殘酷世界之外的夢想。
左翼的悸動,一直是義大利的潛流,從解放神學到帕索里尼,卡爾維諾生平也有過極其義憤填膺直擊不公的時候,但他首先還是忠於文學的公義:寫好一個故事是小說家的天職,是他對敷衍失責的現實的最有力反抗。
他書寫的現實故事結尾往往懸空,讓讀者反覆在落空的角色情感狀態裡受折磨,這樣凜然升起的悲劇精神也屬於左翼文學獨有,卡爾維諾難得完全不動聲色、不加以道德教誨,純粹讓我們被這種殘酷命運所滲透籠罩。
整本小說集的核心,也是最令人捏一把汗的,是中間涉及二戰期間義大利反法西斯游擊隊的篇章,有被捕、轉移、殲滅間諜、面對死亡的種種命運──〈在飯店等死〉就涉及這樣非常時期個體命運的戲劇性交錯,無疑讓我想起卡爾維諾日後的作品《命運交叉的城堡》。
烏鴉和神槍手少年到底誰是死神?
其後〈軍營焦慮症〉等一連串人物似有關聯的抵抗運動主題連作,與另一位法國諾獎作家莫迪亞諾的維希時期法國恰成對比。莫迪亞諾強調的是淪陷時期人受制於命運的惶恐恍惚,卡爾維諾強調的是命運的隙縫,人如何在隙縫中掙扎成為自由的人,而不是被例外狀態吞沒的裸人。
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主題:跑。奔走、逃亡、行軍、迷路。因為書寫人物的快速移動,卡爾維諾盡情顯露他文字的拿手好戲──日後他在《未來文學千年備忘錄》(《 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稱之為「迅捷」的風格。無論逃跑的迅捷還是給游擊隊送信的迅捷,迅捷都源於自由的體會,自由則從政治意義過渡到文學意義,形成小說裡最華彩的段落。〈山麓驚魂〉裡的年輕游擊隊員,讓人想到塔可夫斯基拍攝的《伊凡的少年時代》,少年從焦慮的疾走轉向愛的幻想,再轉向對巨人的幻想,非常童話也非常恐懼,這就是戰爭最恐怖的時刻的狀態,也是自由在走鋼索的狀態。

神乎其技的死亡描寫,出現在本書同題作品〈最後來的是烏鴉〉,這句話本來就是西方黑暗童謠的諺語,表示難以抗拒的命運之虛無力量。在那個被追擊的納粹德國士兵眼中,烏鴉和神槍手少年到底誰是死神?卡爾維諾的敘述自由放肆,越來越神奇超現實──死亡的陰影卻越來越重,但受死的士兵竟然像領受聖禮一樣自然進入了解脫。與之相比的是〈三個之中有一個還活著〉,僥倖不死者也不是神蹟的領受者,他要經歷的是煉獄的雪。
抗戰題材之後是慾望題材,〈動物森林〉成為兩者的完美過渡,它把古典童話模式作為現實荒謬的運用,雜耍演員獻寶式的連串敘述,讓人相信每個義大利人身上都有一個達利歐‧佛(Dario Fo)。同樣運用傳統文學拆東牆補西牆的敘述魔術進行的〈美金和徐娘半老風塵女〉,令人讚嘆的是一場滑稽劇突變成深沉悲劇,卡爾維諾高超的技巧卻渾然不露痕跡;〈糕餅店失竊記〉則相反,以為是悲劇收場的,最後像費里尼的喜劇,與讀得人提心吊膽的〈小兵奇遇記〉一樣,真相是對慾望的真誠歌頌。
卡爾維諾也曾扮演闖進皮草店挑釁的角色
〈十一月的願望〉徹底放開,非常嬉皮非常安那其,總結了之前幾篇的慾望浮動,老嬉皮和無產階級小姑娘睡了一覺,嚴重挑釁了皮草包裹的維納斯那樣的布爾喬亞趣味。我們似乎可以聽到卡爾維諾邊寫邊得意地笑:為什麼不可以呢?
卡爾維諾本身就曾扮演這樣一個闖進皮草店挑釁的角色,他的皮草店是我們熟悉了的、學院化了的先鋒派文學。1957年,在接受一個名為「關於現實主義的若干問題」的訪談中,卡爾維諾這樣定義自己心目中的「政治傾向文學」:「政治傾向文學想要將先鋒派文學的形式和內在的反抗,融入全世界範圍內的社會和政治革命鬥爭當中……但是政治傾向文學並不是單純地記錄重大事件和歷史問題,而是對我們時代的人進行定義……重新爭取人的權利,一種不立即被歷史所利用的權利。」
重新爭取、不被利用,這些社會抗爭中的詞彙,出自文體大師卡爾維諾的筆下,終於也獲得了更自由的氣息。經過了這一番裝備,我們可以和卡爾維諾一起,重新走進那個更宏大變幻的迷宮了。卡爾維諾始終不忘環顧組成迷宮的粗糙的現實主義石牆,我們也最好不要忘記。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